小姨:藏在时光里的暖
小姨:藏在时光里的暖
外婆一生只育了两个女儿,大的是我母亲,小的,便是我记了一辈子、念了一辈子的小姨。
早年间,家里光景天差地别。父亲家有田有酒坊,日子殷实体面,外公便做主,把母亲许配进了我们家。本是门当户对的好姻缘,可解放后划成分,我们家一夜之间被定为地主,从前的安稳尽数散去,往后的日子,只能低着头、谨小慎微地过。
在那段抬不起头的岁月里,小姨是照进我童年里的一束光。
她是外婆最疼的小女儿,嫁得比母亲顺遂安稳,嫁去了南阳东街,做起了小生意,成了正儿八经的城里人家。对困在乡下、尝尽冷眼的我来说,南阳的青石板街巷、热闹喧腾的铺子,是藏着无限新奇与光亮的远方,而远方里最让我魂牵梦绕的,始终是城里那个满心满眼都疼我的小姨。
我打小就爱往小姨家跑,总是攥着衣角,一路小跑着撞开她家的门。小姨一看见我,眉眼立刻弯成了月牙,嘴角的笑意藏都藏不住。她总会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摸出两毛钱,轻轻塞进我手心,那温热的纸币,是我儿时最珍贵、最骄傲的财富。不等我站稳,她便转身钻进厨房,为我张罗吃食:暄软的白面馍、甜香的糖水蛋,每一样都是乡下难得一见的滋味,暖了肠胃,更暖了我那颗敏感自卑的心。等我要离开时,她又会抓上一大把花生、水果糖,把我的衣兜塞得鼓鼓囊囊,叮嘱我带回家慢慢吃,不许一下子吃光。
后来姨夫说要回镇平发展,小姨二话不说,跟着他离开了熟悉的南阳东街。她在家门口支起一个小小的茶摊,烧水、沏茶、招呼客人,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却从未消减过对我的牵挂。镇平离南阳七十里路,坐车要八毛钱车费,路途遥远,一路颠簸,却从来拦不住我想见小姨的心。每到星期六,母亲总会递给我一块钱,让我坐车去寻她。我攥着钱,坐在摇晃的班车上,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前行,心里装的全是欢喜与期盼。
到了小姨的茶摊前,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她依旧会把最好吃的留给我,拉着我的手说尽贴心话,听我讲乡下的琐事,从不嫌我啰嗦。等我要返程回家,她总会趁人不注意,悄悄再塞给我一块钱,轻轻按在我的手心,让我路上买水买零食。一来一回,车费花去八毛,我总能落下几毛钱,那几毛钱在儿时的我眼里,是天大的富足,是小姨藏在掌心、不肯让我受半分委屈的疼爱。
那些年,周六的班车、南阳到镇平的土路、小姨塞钱时温热的手心、兜里沉甸甸的糖果零食,拼凑成了我童年最柔软、最安心的记忆。在我们家最难熬、最灰暗的日子里,在我这个乡下孩子敏感又懵懂的时光里,唯有小姨,不问出身,不计得失,不看成分,把所有的温柔与偏爱,毫无保留地都给了我。她从不说一句心疼的话,却用一次次塞来的钱、一碗碗热乎的饭、一个个装满零食的衣兜,把我的童年捂得暖意融融。
如今时光匆匆走远,日子早已换了崭新的模样,我们再也不用低头过日子,南阳东街的烟火、镇平茶摊的热气,都成了旧时光里的剪影。可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一见我就眉眼含笑的小姨,那个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的小姨。
她的好,不张扬,不浓烈,细细碎碎,藏在流年的缝隙里,藏在岁月的烟火中,岁岁年年,从未褪色。那是时光也带不走的暖,是扎根在我心底、伴我一生的温柔,是我这辈子想起,就会鼻尖发酸、心头滚烫的牵挂。
外婆一生只育了两个女儿,大的是我母亲,小的,便是我记了一辈子、念了一辈子的小姨。
早年间,家里光景天差地别。父亲家有田有酒坊,日子殷实体面,外公便做主,把母亲许配进了我们家。本是门当户对的好姻缘,可解放后划成分,我们家一夜之间被定为地主,从前的安稳尽数散去,往后的日子,只能低着头、谨小慎微地过。
在那段抬不起头的岁月里,小姨是照进我童年里的一束光。
她是外婆最疼的小女儿,嫁得比母亲顺遂安稳,嫁去了南阳东街,做起了小生意,成了正儿八经的城里人家。对困在乡下、尝尽冷眼的我来说,南阳的青石板街巷、热闹喧腾的铺子,是藏着无限新奇与光亮的远方,而远方里最让我魂牵梦绕的,始终是城里那个满心满眼都疼我的小姨。
我打小就爱往小姨家跑,总是攥着衣角,一路小跑着撞开她家的门。小姨一看见我,眉眼立刻弯成了月牙,嘴角的笑意藏都藏不住。她总会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摸出两毛钱,轻轻塞进我手心,那温热的纸币,是我儿时最珍贵、最骄傲的财富。不等我站稳,她便转身钻进厨房,为我张罗吃食:暄软的白面馍、甜香的糖水蛋,每一样都是乡下难得一见的滋味,暖了肠胃,更暖了我那颗敏感自卑的心。等我要离开时,她又会抓上一大把花生、水果糖,把我的衣兜塞得鼓鼓囊囊,叮嘱我带回家慢慢吃,不许一下子吃光。
后来姨夫说要回镇平发展,小姨二话不说,跟着他离开了熟悉的南阳东街。她在家门口支起一个小小的茶摊,烧水、沏茶、招呼客人,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却从未消减过对我的牵挂。镇平离南阳七十里路,坐车要八毛钱车费,路途遥远,一路颠簸,却从来拦不住我想见小姨的心。每到星期六,母亲总会递给我一块钱,让我坐车去寻她。我攥着钱,坐在摇晃的班车上,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前行,心里装的全是欢喜与期盼。
到了小姨的茶摊前,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她依旧会把最好吃的留给我,拉着我的手说尽贴心话,听我讲乡下的琐事,从不嫌我啰嗦。等我要返程回家,她总会趁人不注意,悄悄再塞给我一块钱,轻轻按在我的手心,让我路上买水买零食。一来一回,车费花去八毛,我总能落下几毛钱,那几毛钱在儿时的我眼里,是天大的富足,是小姨藏在掌心、不肯让我受半分委屈的疼爱。
那些年,周六的班车、南阳到镇平的土路、小姨塞钱时温热的手心、兜里沉甸甸的糖果零食,拼凑成了我童年最柔软、最安心的记忆。在我们家最难熬、最灰暗的日子里,在我这个乡下孩子敏感又懵懂的时光里,唯有小姨,不问出身,不计得失,不看成分,把所有的温柔与偏爱,毫无保留地都给了我。她从不说一句心疼的话,却用一次次塞来的钱、一碗碗热乎的饭、一个个装满零食的衣兜,把我的童年捂得暖意融融。
如今时光匆匆走远,日子早已换了崭新的模样,我们再也不用低头过日子,南阳东街的烟火、镇平茶摊的热气,都成了旧时光里的剪影。可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一见我就眉眼含笑的小姨,那个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的小姨。
她的好,不张扬,不浓烈,细细碎碎,藏在流年的缝隙里,藏在岁月的烟火中,岁岁年年,从未褪色。那是时光也带不走的暖,是扎根在我心底、伴我一生的温柔,是我这辈子想起,就会鼻尖发酸、心头滚烫的牵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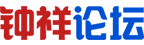

赞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