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药香和硬心肠
在我的记忆里,总有一股淡淡的药香,那是外婆身上独有的味道。她看似有着一副硬心肠,却把最温柔的疼爱,全都藏在了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守护里。
我总觉得,外婆的一辈子,是被灶台的烟火、院里的药香,还有一口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的训话声,满满当当填满的。
她是个直爽到藏不住半句话的人,手脚比嘴还要麻利。家里的角角落落永远被她收拾得井井有条,抹布叠得方方正正,碗筷摆得整整齐齐,连扫过的地都透着一股清爽干净的劲儿。大舅、小舅、我妈、小姨,四个孩子全是她一手拉扯大的,白天围着灶台转,夜里就着油灯缝补衣裳,一辈子没喊过一声苦,没说过一句累。那时候日子难,她不光要把家务打理得妥帖周全,还要跟着外公上山种药草、回来晒药草。太阳最毒的正午,她蹲在晒场上一遍遍翻晒草药,汗水顺着深深的皱纹往下淌,也只是抬手随意抹一把,弯着腰继续干活。草药清苦又安心的气息,成了我童年里最踏实的味道,那是外婆用一生的勤劳,一点点熬出来的安稳。
外婆疼我们这些孙辈,是藏在骨头里的,可她的爱,从来不带半分袒护。我是她最偏爱的小外孙,可这份偏爱,从来不是纵容。别的老人会把好吃的偷偷塞给孙儿,任由我们胡闹撒野,外婆不。她眼里揉不得沙子,谁要是不听话、做错事,她那张直爽的嘴绝不会饶人,声音不大,却字字有力,不拐弯抹角,也从不放任姑息。
我至今记得几件小事,想起来又暖又酸,一闭眼,就能看见当年的模样。
那年夏天,我馋得厉害,偷偷把外婆晒在竹匾里的金银花抓了一大把,跑到后山和小伙伴换了冰棍。那是外公特意种的药材,要晒干了卖钱补贴家用,是外婆顶着烈日,守着太阳翻晒了好几天的宝贝。等我啃着甜丝丝的冰棍回家,外婆只一眼,就看出了端倪,脸色立刻沉了下来。她没骂脏话,也没动手,只是拉着我坐在堂屋的小板凳上,一字一句问我东西去哪了。我一开始还想撒谎,可被她沉静又严厉的目光看得心慌,支支吾吾说了实话。
那天外婆真的生气了。她指着空了一角的竹匾,严肃地告诉我:“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药材是我和你外公顶着大太阳一棵一棵种出来的,不是让你拿去换零食的。做人第一要诚实,第二要懂珍惜,错了就要认,不能嘴硬。”她让我站在墙角认错,不许吃晚饭,直到我真心哭着道歉,她才松了口。可夜里我饿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却闻到厨房飘来一阵温热的香味——外婆悄悄给我煮了鸡蛋面,还往我碗里卧了两个圆滚滚的荷包蛋。她坐在一旁看着我狼吞虎咽,轻声说:“不是外婆小气,是怕你从小不学好,长大了走歪路。”那碗面的温度,我记了好多年。
还有一回,是连着下了好几天的暴雨,后山的药田被淹了大半。外公急得睡不着,天不亮就往山上跑,外婆更是一夜没合眼,天刚蒙蒙亮就扛起锄头、拎着麻袋跟了上去。泥泞的山路又滑又难走,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水里,把还能救活的药草一棵一棵挖出来,根上裹着泥,她就用冻得发红的手一点点抠干净。雨水打湿了她的头发和衣服,贴在额头上、背上,她也顾不上擦,只是埋头抢救那些维系着家用的药材。
回到家,她顾不上换一身干衣服,立刻把救回来的药草分门别类,铺在堂屋的地上、桌上,拿着蒲扇一扇就是大半天。那几天,她白天打理家务、照看药草,夜里还要操心一家人的吃喝,眼睛里全是红血丝,却从没说过一句累,也没叹过一声气。我那时候小,看着外婆忙碌的身影,只觉得她像一棵永远不会倒下的老树,稳稳地撑着整个家。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打心底里佩服外婆的坚韧和能干,也更懂她平日里对每一样东西都格外珍惜的原因。
我总忘了说,还有一次深夜的药香,刻在我心底最软的地方。
小时候我体质弱,一到换季就咳嗽不止。外婆从不带我乱吃药,只在夜里悄悄起身,把晒干的枇杷叶、桑叶、甘草一点点洗净,放进小砂锅里慢火熬煮。昏黄的灯光下,她坐在灶台边,一边添柴,一边轻轻扇风,药香一点点漫出来,裹着烟火气,温柔得不像平日里那个严厉的外婆。熬好后,她会放一勺冰糖晾温,再端到我床边,看着我一口口喝下去,才轻轻掖好被角。她从不说软话,可那碗不苦不涩的药汤,比任何安慰都更暖。
那时候的我,又怕她,又依赖她。我佩服她一辈子硬气、勤劳、把日子过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怕她毫不留情的训教。可长大以后才慢慢明白,外婆的严厉,是最踏实的疼爱;她的训教,是给我一辈子用不完的底气。
后来我走了很远的路,见过很多人,却再也没遇到像外婆那样的人。她的直爽,她的勤劳,她藏在严厉里的温柔,还有院子里晒不尽、散不开的药草香,成了我记忆里最温暖、也最有力量的光。外婆的故事很长,长到裹着一辈子的风霜雨雪,也长到够我记一辈子,念一辈子,暖一辈子。
如今我渐渐长大,才真正懂得:外婆的硬心肠,从来不是冷漠,而是怕我受委屈、怕我走弯路。那缕挥之不去的药香,和她看似强硬的温柔,早已成为我生命里最温暖、最安心的光。
我总觉得,外婆的一辈子,是被灶台的烟火、院里的药香,还有一口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的训话声,满满当当填满的。
她是个直爽到藏不住半句话的人,手脚比嘴还要麻利。家里的角角落落永远被她收拾得井井有条,抹布叠得方方正正,碗筷摆得整整齐齐,连扫过的地都透着一股清爽干净的劲儿。大舅、小舅、我妈、小姨,四个孩子全是她一手拉扯大的,白天围着灶台转,夜里就着油灯缝补衣裳,一辈子没喊过一声苦,没说过一句累。那时候日子难,她不光要把家务打理得妥帖周全,还要跟着外公上山种药草、回来晒药草。太阳最毒的正午,她蹲在晒场上一遍遍翻晒草药,汗水顺着深深的皱纹往下淌,也只是抬手随意抹一把,弯着腰继续干活。草药清苦又安心的气息,成了我童年里最踏实的味道,那是外婆用一生的勤劳,一点点熬出来的安稳。
外婆疼我们这些孙辈,是藏在骨头里的,可她的爱,从来不带半分袒护。我是她最偏爱的小外孙,可这份偏爱,从来不是纵容。别的老人会把好吃的偷偷塞给孙儿,任由我们胡闹撒野,外婆不。她眼里揉不得沙子,谁要是不听话、做错事,她那张直爽的嘴绝不会饶人,声音不大,却字字有力,不拐弯抹角,也从不放任姑息。
我至今记得几件小事,想起来又暖又酸,一闭眼,就能看见当年的模样。
那年夏天,我馋得厉害,偷偷把外婆晒在竹匾里的金银花抓了一大把,跑到后山和小伙伴换了冰棍。那是外公特意种的药材,要晒干了卖钱补贴家用,是外婆顶着烈日,守着太阳翻晒了好几天的宝贝。等我啃着甜丝丝的冰棍回家,外婆只一眼,就看出了端倪,脸色立刻沉了下来。她没骂脏话,也没动手,只是拉着我坐在堂屋的小板凳上,一字一句问我东西去哪了。我一开始还想撒谎,可被她沉静又严厉的目光看得心慌,支支吾吾说了实话。
那天外婆真的生气了。她指着空了一角的竹匾,严肃地告诉我:“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药材是我和你外公顶着大太阳一棵一棵种出来的,不是让你拿去换零食的。做人第一要诚实,第二要懂珍惜,错了就要认,不能嘴硬。”她让我站在墙角认错,不许吃晚饭,直到我真心哭着道歉,她才松了口。可夜里我饿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却闻到厨房飘来一阵温热的香味——外婆悄悄给我煮了鸡蛋面,还往我碗里卧了两个圆滚滚的荷包蛋。她坐在一旁看着我狼吞虎咽,轻声说:“不是外婆小气,是怕你从小不学好,长大了走歪路。”那碗面的温度,我记了好多年。
还有一回,是连着下了好几天的暴雨,后山的药田被淹了大半。外公急得睡不着,天不亮就往山上跑,外婆更是一夜没合眼,天刚蒙蒙亮就扛起锄头、拎着麻袋跟了上去。泥泞的山路又滑又难走,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水里,把还能救活的药草一棵一棵挖出来,根上裹着泥,她就用冻得发红的手一点点抠干净。雨水打湿了她的头发和衣服,贴在额头上、背上,她也顾不上擦,只是埋头抢救那些维系着家用的药材。
回到家,她顾不上换一身干衣服,立刻把救回来的药草分门别类,铺在堂屋的地上、桌上,拿着蒲扇一扇就是大半天。那几天,她白天打理家务、照看药草,夜里还要操心一家人的吃喝,眼睛里全是红血丝,却从没说过一句累,也没叹过一声气。我那时候小,看着外婆忙碌的身影,只觉得她像一棵永远不会倒下的老树,稳稳地撑着整个家。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打心底里佩服外婆的坚韧和能干,也更懂她平日里对每一样东西都格外珍惜的原因。
我总忘了说,还有一次深夜的药香,刻在我心底最软的地方。
小时候我体质弱,一到换季就咳嗽不止。外婆从不带我乱吃药,只在夜里悄悄起身,把晒干的枇杷叶、桑叶、甘草一点点洗净,放进小砂锅里慢火熬煮。昏黄的灯光下,她坐在灶台边,一边添柴,一边轻轻扇风,药香一点点漫出来,裹着烟火气,温柔得不像平日里那个严厉的外婆。熬好后,她会放一勺冰糖晾温,再端到我床边,看着我一口口喝下去,才轻轻掖好被角。她从不说软话,可那碗不苦不涩的药汤,比任何安慰都更暖。
那时候的我,又怕她,又依赖她。我佩服她一辈子硬气、勤劳、把日子过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怕她毫不留情的训教。可长大以后才慢慢明白,外婆的严厉,是最踏实的疼爱;她的训教,是给我一辈子用不完的底气。
后来我走了很远的路,见过很多人,却再也没遇到像外婆那样的人。她的直爽,她的勤劳,她藏在严厉里的温柔,还有院子里晒不尽、散不开的药草香,成了我记忆里最温暖、也最有力量的光。外婆的故事很长,长到裹着一辈子的风霜雨雪,也长到够我记一辈子,念一辈子,暖一辈子。
如今我渐渐长大,才真正懂得:外婆的硬心肠,从来不是冷漠,而是怕我受委屈、怕我走弯路。那缕挥之不去的药香,和她看似强硬的温柔,早已成为我生命里最温暖、最安心的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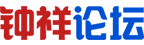

赞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