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洞里的青春印记
窑洞里的青春印记
一九六八年九月,秋风卷着黄土掠过晋南的山塬。我背着捆着衣物的帆布包,随着下乡队伍踏上了山西翼城的土地。卡车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颠簸许久,最终停在中卫公社武子官庄村口。
我们从不同的地方下放到山西翼城中卫公社武子官庄村,四个男生两个女生,被领到了村西头的两间旧窑洞前。这便是我们往后不知要住多久的家。
刚到这里,团支书张立业和大队会计冯家德就找上了我们。他们一是让我们参加俱乐部,排演文艺节目;二是让我们把节目带到中卫公社演出。由我编演的《武子官庄我的家》还获了奖,这让我们初来乍到的心,多了一丝慰藉。
但新鲜感很快被现实冲淡。窑洞低矮昏暗,墙皮有些地方已经剥落,糊着旧报纸的窗棂透着微弱的光。男生住外间,女生住里间,中间只隔着一道薄薄的木门。行李还没来得及归置,蚊子便像闻到了新鲜气息的小贼,成群结队地涌了进来。它们个头大,叮人极狠,一巴掌拍下去能溅出暗红的血。
那天夜里,我们轮换着用蒲扇拍打,嗡嗡声却始终绕耳不绝。到天快亮时,每个人胳膊腿上都布满了红肿的疙瘩,几乎没合上过眼。
比蚊子更磨人的是吃水的难题。村里没有水井,用水得去一里多地外的山洼沟挑。起初,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根本不会挑扁担。扁担刚上肩就晃得厉害,走两步水就洒一半,到了窑洞前桶里只剩个底儿。
有次我逞强挑着满桶水往回走,脚下一滑摔在土坡上。不仅浑身是泥,水桶也摔裂了缝。队里的老支书看在眼里,第二天特意找来根磨得光滑的扁担,手把手教我们挑水的诀窍:“肩膀要稳,步子要匀,腰杆得撑住劲儿。”
日子就在挑水、下地、啃窝头的循环里慢慢过着。我们渐渐学会了跟黄土打交道,手上的茧子磨厚了,挑水的脚步也稳了。直到那年冬天,一场大雪突如其来,从清晨下到日暮,天地间白茫茫一片,连窑洞门口的路都被积雪埋了半截。
队里放了假,不用下地挣工分,我们索性缩在窑洞里。男生们裹着打补丁的棉被挤在土炕上,女生们靠着墙织毛衣,谁也不愿冒着寒风出去。窑洞里没有生炉子,冷得人直跺脚。我们就轮流讲城里的故事,讲家里的饭菜,讲着讲着,声音就低了下去,只剩下窗外雪花飘落的簌簌声。
后来的日子里,我们跟着村民学种玉米、摘棉花,在煤油灯下写家书,在田埂上唱红歌。旧窑洞的墙皮补了又掉,挑水的扁担换了又换,蚊子依旧每年夏天准时出现。但我们再也不会因为蚊虫叮咬彻夜难眠,也能挑着满满两桶水健步如飞。
如今再想起武子官庄村的那些年,最先浮现在眼前的不是蚊子的叮咬,也不是挑水的艰辛,而是雪天窑洞里此起彼伏的叹息与欢笑,是老支书递来扁担时粗糙的手掌,是六个年轻人在黄土塬上相互扶持的身影。那些藏在窑洞里的日子,那些浸着汗水与思念的时光,早已成了青春里最深刻的印记,在岁月里愈发清晰。
一九六八年九月,秋风卷着黄土掠过晋南的山塬。我背着捆着衣物的帆布包,随着下乡队伍踏上了山西翼城的土地。卡车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颠簸许久,最终停在中卫公社武子官庄村口。
我们从不同的地方下放到山西翼城中卫公社武子官庄村,四个男生两个女生,被领到了村西头的两间旧窑洞前。这便是我们往后不知要住多久的家。
刚到这里,团支书张立业和大队会计冯家德就找上了我们。他们一是让我们参加俱乐部,排演文艺节目;二是让我们把节目带到中卫公社演出。由我编演的《武子官庄我的家》还获了奖,这让我们初来乍到的心,多了一丝慰藉。
但新鲜感很快被现实冲淡。窑洞低矮昏暗,墙皮有些地方已经剥落,糊着旧报纸的窗棂透着微弱的光。男生住外间,女生住里间,中间只隔着一道薄薄的木门。行李还没来得及归置,蚊子便像闻到了新鲜气息的小贼,成群结队地涌了进来。它们个头大,叮人极狠,一巴掌拍下去能溅出暗红的血。
那天夜里,我们轮换着用蒲扇拍打,嗡嗡声却始终绕耳不绝。到天快亮时,每个人胳膊腿上都布满了红肿的疙瘩,几乎没合上过眼。
比蚊子更磨人的是吃水的难题。村里没有水井,用水得去一里多地外的山洼沟挑。起初,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根本不会挑扁担。扁担刚上肩就晃得厉害,走两步水就洒一半,到了窑洞前桶里只剩个底儿。
有次我逞强挑着满桶水往回走,脚下一滑摔在土坡上。不仅浑身是泥,水桶也摔裂了缝。队里的老支书看在眼里,第二天特意找来根磨得光滑的扁担,手把手教我们挑水的诀窍:“肩膀要稳,步子要匀,腰杆得撑住劲儿。”
日子就在挑水、下地、啃窝头的循环里慢慢过着。我们渐渐学会了跟黄土打交道,手上的茧子磨厚了,挑水的脚步也稳了。直到那年冬天,一场大雪突如其来,从清晨下到日暮,天地间白茫茫一片,连窑洞门口的路都被积雪埋了半截。
队里放了假,不用下地挣工分,我们索性缩在窑洞里。男生们裹着打补丁的棉被挤在土炕上,女生们靠着墙织毛衣,谁也不愿冒着寒风出去。窑洞里没有生炉子,冷得人直跺脚。我们就轮流讲城里的故事,讲家里的饭菜,讲着讲着,声音就低了下去,只剩下窗外雪花飘落的簌簌声。
后来的日子里,我们跟着村民学种玉米、摘棉花,在煤油灯下写家书,在田埂上唱红歌。旧窑洞的墙皮补了又掉,挑水的扁担换了又换,蚊子依旧每年夏天准时出现。但我们再也不会因为蚊虫叮咬彻夜难眠,也能挑着满满两桶水健步如飞。
如今再想起武子官庄村的那些年,最先浮现在眼前的不是蚊子的叮咬,也不是挑水的艰辛,而是雪天窑洞里此起彼伏的叹息与欢笑,是老支书递来扁担时粗糙的手掌,是六个年轻人在黄土塬上相互扶持的身影。那些藏在窑洞里的日子,那些浸着汗水与思念的时光,早已成了青春里最深刻的印记,在岁月里愈发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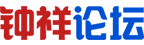

赞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