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河水:故城南阳的生命之泉
白河水:故城南阳的生命之泉
南阳南关的水门城楼,青砖被岁月浸成了深灰,墙缝里钻着半枯的茅草,像老人下巴上的胡须。城门洞上方的“通济门”石匾,字迹被风雨磨得有些模糊,唯有边缘的卷草纹,还能看出当年的精致。墙面上布满深浅不一的水痕,那是白河涨水时留下的印记,一道叠着一道,像老南阳人额头的皱纹,藏着说不尽的故事。城门下的石板路,被一代代拉水、挑水人的脚步磨得发亮,两道深深的车辙沟,嵌在石板里,积着昨夜的雨水,映着城楼的影子,成了白河滋养南阳最鲜活的证明。
天还没亮透,水门楼下的雾气还没散尽,挑水的队伍就从城门根排到了河岸边。打头的汉子光着黝黑的脊梁,古铜色的皮肤上渗着细密的汗珠,扁担压在肩头,把粗布褂子的肩头磨出了一个发亮的补丁。他双手扶着扁担,腰微微弓着,每走一步,扁担就发出“咯吱”一声响,像是在哼着老南阳的调子。木桶是厚铁皮做的,外面包着一层经年累月浸出的红褐色水锈,提手处被手掌磨得油光锃亮,泛着温润的光。
拉水的马车紧随其后,骡马的鬃毛上挂着晨露,响鼻“呼哧呼哧”地喷着白气,蹄子踏在石板路上,敲出“哒哒”的脆响。车夫穿着打补丁的蓝布衫,坐在车辕上,手里的鞭子梢系着红布条,轻轻一扬,红布条就在雾里划了道弧线,却从不真往骡马身上落。车厢里的大水箱用粗麻绳捆得结实,木板缝里渗出的水珠子,顺着车厢壁往下滴,在石板路上积成小小的水洼,映着天边刚冒头的鱼肚白。有调皮的孩子追着马车跑,伸手去接那些滴落的水珠,惹得车夫哈哈大笑。
我小时候总爱跟着奶奶来水门楼。她的小木桶比别人的轻,桶沿上还缠着一圈防滑的蓝布条,却也得来回两趟才能装满家里的水缸。我就蹲在石板上,看挑水的汉子们把桶往河里一沉,手腕轻轻一转,桶就“咕咚”一声灌满了水,提上来时,水面上还漂着一两片嫩绿水草。奶奶一边用葫芦瓢往桶里舀水,一边用袖口擦着额角的汗,念叨着:“咱南阳人都是喝白河的水长大的!这水甜津津、凉丝丝的,比啥糖水都养人。你看那城墙根的老槐树,喝着白河的水,都活了上百年咧!”
如今水门楼下的石板路不再拥挤,家家户户都通了自来水,可那两道车辙沟还留在那里,像白河刻在南阳城身上的年轮。每次路过,我都会停下脚步摸一摸那些光滑的石板,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的脚步声、车铃声,还有白河水流过城门的声音。这水门,这石板路,这白河,早就把根扎在了南阳人的心里,一代又一代,从未改变。
南阳南关的水门城楼,青砖被岁月浸成了深灰,墙缝里钻着半枯的茅草,像老人下巴上的胡须。城门洞上方的“通济门”石匾,字迹被风雨磨得有些模糊,唯有边缘的卷草纹,还能看出当年的精致。墙面上布满深浅不一的水痕,那是白河涨水时留下的印记,一道叠着一道,像老南阳人额头的皱纹,藏着说不尽的故事。城门下的石板路,被一代代拉水、挑水人的脚步磨得发亮,两道深深的车辙沟,嵌在石板里,积着昨夜的雨水,映着城楼的影子,成了白河滋养南阳最鲜活的证明。
天还没亮透,水门楼下的雾气还没散尽,挑水的队伍就从城门根排到了河岸边。打头的汉子光着黝黑的脊梁,古铜色的皮肤上渗着细密的汗珠,扁担压在肩头,把粗布褂子的肩头磨出了一个发亮的补丁。他双手扶着扁担,腰微微弓着,每走一步,扁担就发出“咯吱”一声响,像是在哼着老南阳的调子。木桶是厚铁皮做的,外面包着一层经年累月浸出的红褐色水锈,提手处被手掌磨得油光锃亮,泛着温润的光。
拉水的马车紧随其后,骡马的鬃毛上挂着晨露,响鼻“呼哧呼哧”地喷着白气,蹄子踏在石板路上,敲出“哒哒”的脆响。车夫穿着打补丁的蓝布衫,坐在车辕上,手里的鞭子梢系着红布条,轻轻一扬,红布条就在雾里划了道弧线,却从不真往骡马身上落。车厢里的大水箱用粗麻绳捆得结实,木板缝里渗出的水珠子,顺着车厢壁往下滴,在石板路上积成小小的水洼,映着天边刚冒头的鱼肚白。有调皮的孩子追着马车跑,伸手去接那些滴落的水珠,惹得车夫哈哈大笑。
我小时候总爱跟着奶奶来水门楼。她的小木桶比别人的轻,桶沿上还缠着一圈防滑的蓝布条,却也得来回两趟才能装满家里的水缸。我就蹲在石板上,看挑水的汉子们把桶往河里一沉,手腕轻轻一转,桶就“咕咚”一声灌满了水,提上来时,水面上还漂着一两片嫩绿水草。奶奶一边用葫芦瓢往桶里舀水,一边用袖口擦着额角的汗,念叨着:“咱南阳人都是喝白河的水长大的!这水甜津津、凉丝丝的,比啥糖水都养人。你看那城墙根的老槐树,喝着白河的水,都活了上百年咧!”
如今水门楼下的石板路不再拥挤,家家户户都通了自来水,可那两道车辙沟还留在那里,像白河刻在南阳城身上的年轮。每次路过,我都会停下脚步摸一摸那些光滑的石板,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的脚步声、车铃声,还有白河水流过城门的声音。这水门,这石板路,这白河,早就把根扎在了南阳人的心里,一代又一代,从未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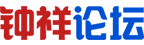

赞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