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
我的童年,总与一方满是药香的小院缠绕。那时父亲因政治运动常遭批斗,母亲怕那些风雨伤了我幼小的心,早早将我送到了外公身边——他是偏僻乡里的土医生,也是我童年最安稳的避风港。
外公的院子从不是寻常模样,门前屋后都被药材占满了。瓜蒌藤蔓爬满竹架,垂着一个个青绿色的果实;麦冬在地上铺成一片细密的绿毯,叶片间藏着小小的花苞;金银花更淘气,顺着土墙往上攀,开得满院都是白的、黄的花。外公总在院里忙,施肥、剪枝、松土,身影在藤蔓间穿梭。我跟在他身后,踮着脚帮他提水桶浇苗,指尖沾着泥土,鼻尖萦绕着药材的清香,那味道,是我童年最安心的背景音。
外公虽是土郎中,手里的土方子却救过不少乡邻。我至今记得那个闹大疮的小孩,脑后脖子上肿起一个吓人的脓包,哭了几天几夜,家人急得团团转。外公没先动手,反倒掏出糖果,又端来温好的蜂蜜水,笑着哄那孩子。小孩盯着外公慈祥的脸,渐渐止了哭;外公又拿一把小木梳,轻轻梳他的头发,痒得孩子咯咯笑起来。就在这笑声里,外公从棉花团里悄悄抽出一把小刀,快准地划开大疮,脓血水溅了我一脸。我没怕,反倒偷偷擦了擦脸,觉得外公像个会变魔术的人。后来每次换药,外公都让我来帮忙,看着那疮口一天天缩小,直到一周后彻底愈合,我才懂,外公的“魔术”里,藏着的是细心与底气。
有一年县里要求种牛痘,说是能预防天花——那时大家都怕得天花,一旦染上,脸上就会留下坑坑洼洼的麻子,要跟着一辈子。疫苗发到乡里,外公接了三个村的接种任务。他让我和表姐当帮手,教我们用针轻轻刺破上臂三角肌的皮肤,滴上一滴疫苗,每次划两点、滴两滴,就算完成了。接种后,大部分人的伤口会红肿,外公说那是成功的信号。那段日子,外公起早贪黑,天不亮就带着我们赶路,直到天黑才回院,整整忙了七天,才把三个村的牛痘都种完。夜里我揉着酸困的胳膊,外公却笑着给我们煮红糖姜茶,说:“多救一个人,心里就多踏实一分。”
外公还总教我认药方、记汤头。他看病时开处方,会让我在一旁看着,等病人走了,就让我照着方子抓药。时间久了,我也能背下些常用的方子。有次邻村来个中年男人,捂着右下腹喊疼,外公曾跟我说过,这种疼加大便不通叫“结症”,就是后来人说的阑尾炎。他看着我,说:“你来开方试试。”我攥着药方纸,想起“大黄牡丹皮汤”,一笔一划写下药名,抓了三付药。后来那男人来说,吃了两付就不疼了,我心里满是雀跃,外公拍着我的头说:“看病要用心,不能只记方子,要懂病的根。”
最难忘的是给妈妈看病。那年我八岁,妈妈突然不吃饭,还总想吐。外公让我先诊诊看,我心里既紧张又兴奋。起初以为是胃病,可仔细一看,妈妈的眼睛有点发黄,我想起外公说的“眼黄、尿黄要留心”,忙问妈妈尿色怎么样。妈妈说尿少又黄,我又看了她的舌苔,心里有了底,小声说:“可能是急性黄疸肝炎。”外公点点头:“那你就开‘茵陈汤’吧。”我照着记忆抓了药,妈妈连服三付,眼黄慢慢退了,上腹部的饱胀感也没了,渐渐能吃饭了。看着妈妈好起来,我第一次觉得,外公教我的不只是药方,更是能守护亲人的力量。
外公离开我已经几十年了,可那方飘着药香的小院,他哄孩子时的笑容,教我认药时的耐心,还有那些治病救人的小事,都像刻在我心里的印记,从未褪色。每当想起他,鼻尖仿佛又能闻到那熟悉的药香,暖得让人想哭——那是外公的味道,是爱与责任的味道,会陪我一辈子。
外公的院子从不是寻常模样,门前屋后都被药材占满了。瓜蒌藤蔓爬满竹架,垂着一个个青绿色的果实;麦冬在地上铺成一片细密的绿毯,叶片间藏着小小的花苞;金银花更淘气,顺着土墙往上攀,开得满院都是白的、黄的花。外公总在院里忙,施肥、剪枝、松土,身影在藤蔓间穿梭。我跟在他身后,踮着脚帮他提水桶浇苗,指尖沾着泥土,鼻尖萦绕着药材的清香,那味道,是我童年最安心的背景音。
外公虽是土郎中,手里的土方子却救过不少乡邻。我至今记得那个闹大疮的小孩,脑后脖子上肿起一个吓人的脓包,哭了几天几夜,家人急得团团转。外公没先动手,反倒掏出糖果,又端来温好的蜂蜜水,笑着哄那孩子。小孩盯着外公慈祥的脸,渐渐止了哭;外公又拿一把小木梳,轻轻梳他的头发,痒得孩子咯咯笑起来。就在这笑声里,外公从棉花团里悄悄抽出一把小刀,快准地划开大疮,脓血水溅了我一脸。我没怕,反倒偷偷擦了擦脸,觉得外公像个会变魔术的人。后来每次换药,外公都让我来帮忙,看着那疮口一天天缩小,直到一周后彻底愈合,我才懂,外公的“魔术”里,藏着的是细心与底气。
有一年县里要求种牛痘,说是能预防天花——那时大家都怕得天花,一旦染上,脸上就会留下坑坑洼洼的麻子,要跟着一辈子。疫苗发到乡里,外公接了三个村的接种任务。他让我和表姐当帮手,教我们用针轻轻刺破上臂三角肌的皮肤,滴上一滴疫苗,每次划两点、滴两滴,就算完成了。接种后,大部分人的伤口会红肿,外公说那是成功的信号。那段日子,外公起早贪黑,天不亮就带着我们赶路,直到天黑才回院,整整忙了七天,才把三个村的牛痘都种完。夜里我揉着酸困的胳膊,外公却笑着给我们煮红糖姜茶,说:“多救一个人,心里就多踏实一分。”
外公还总教我认药方、记汤头。他看病时开处方,会让我在一旁看着,等病人走了,就让我照着方子抓药。时间久了,我也能背下些常用的方子。有次邻村来个中年男人,捂着右下腹喊疼,外公曾跟我说过,这种疼加大便不通叫“结症”,就是后来人说的阑尾炎。他看着我,说:“你来开方试试。”我攥着药方纸,想起“大黄牡丹皮汤”,一笔一划写下药名,抓了三付药。后来那男人来说,吃了两付就不疼了,我心里满是雀跃,外公拍着我的头说:“看病要用心,不能只记方子,要懂病的根。”
最难忘的是给妈妈看病。那年我八岁,妈妈突然不吃饭,还总想吐。外公让我先诊诊看,我心里既紧张又兴奋。起初以为是胃病,可仔细一看,妈妈的眼睛有点发黄,我想起外公说的“眼黄、尿黄要留心”,忙问妈妈尿色怎么样。妈妈说尿少又黄,我又看了她的舌苔,心里有了底,小声说:“可能是急性黄疸肝炎。”外公点点头:“那你就开‘茵陈汤’吧。”我照着记忆抓了药,妈妈连服三付,眼黄慢慢退了,上腹部的饱胀感也没了,渐渐能吃饭了。看着妈妈好起来,我第一次觉得,外公教我的不只是药方,更是能守护亲人的力量。
外公离开我已经几十年了,可那方飘着药香的小院,他哄孩子时的笑容,教我认药时的耐心,还有那些治病救人的小事,都像刻在我心里的印记,从未褪色。每当想起他,鼻尖仿佛又能闻到那熟悉的药香,暖得让人想哭——那是外公的味道,是爱与责任的味道,会陪我一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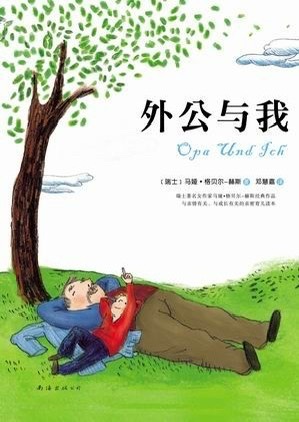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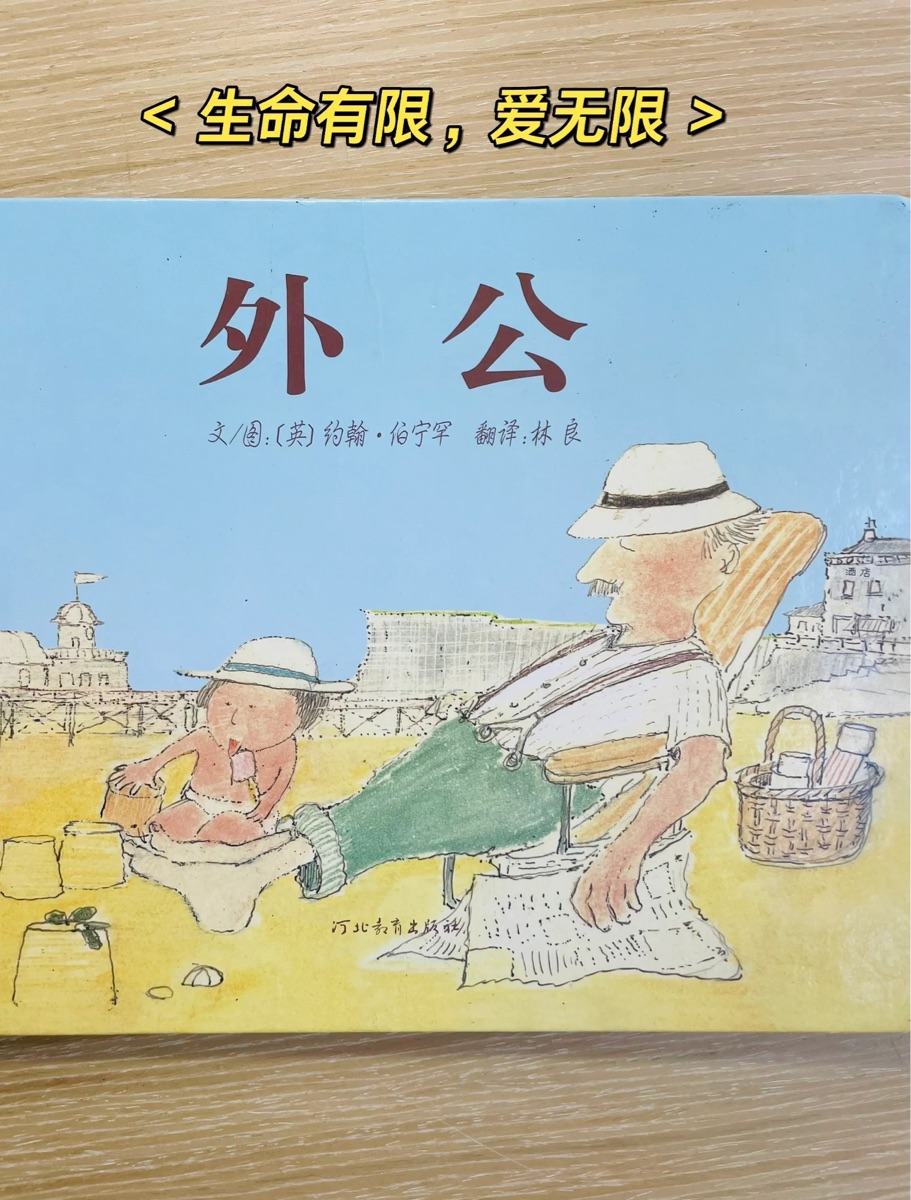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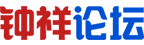

赞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