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坊浮沉里的光阴
酒坊浮沉里的光阴
解放的锣鼓声还在村口回响时,父亲的老酒坊却先迎来了寒霜。那天几个穿干部服的人走进巷子,青石板路上的脚步声格外沉,他们指着酒坊里帮忙的王叔、表伯们,说父亲这是“剥削”,不容分说便让帮工们回了家。
父亲站在空荡荡的酒坊里,看着蒙了薄尘的酒缸和静置的木甑,没争辩一句。先前他总天不亮就查窖温,夜里还对着账本盘算帮工的工钱,如今倒真成了“不操心”的人,只是吃饭时总盯着墙角那根竹探杆发愣。
没几日,王叔领着表伯们找上了门。都是沾亲带故的,谁家日子都紧巴,没了酒坊的活计,连买盐的钱都凑不齐,更别提拖欠的工钱了。“哥,咱偷偷开吧,就做街坊的生意,没人知道。”王叔搓着手说。父亲沉默半晌,终是叹了口气,重新掀开了酒缸上的棉布。
酒坊又热闹起来,蒸米的白汽、拌曲的声响、醇厚的酒香,悄悄漫回了巷子。父亲依旧把活计做得精细,只是收工后总会多张望几眼巷口。可安稳日子没撑过俩月,一个陌生男人推开了酒坊门,自称是税务员,说酒坊要交税,还要罚200元。
“200元?”父亲手里的竹探杆“当啷”掉在地上。那时全家一年到头忙活,收入也才20元。他连夜把酒缸、木甑低价卖给了邻村的杂货铺,又牵走了家里唯一的老黄牛,可凑来的钱连零头都不够。税务员走时撂下的话,像块石头压得他直不起腰。
那天晚上,父亲坐在空酒坊里,摸了摸冰冷的灶台,一夜没合眼。后来,巷口的木门再也没为酿酒开过,那些蒙着棉布的酒缸渐渐积满了灰,连空气里的酒糟香,都慢慢淡成了回忆。
解放的锣鼓声还在村口回响时,父亲的老酒坊却先迎来了寒霜。那天几个穿干部服的人走进巷子,青石板路上的脚步声格外沉,他们指着酒坊里帮忙的王叔、表伯们,说父亲这是“剥削”,不容分说便让帮工们回了家。
父亲站在空荡荡的酒坊里,看着蒙了薄尘的酒缸和静置的木甑,没争辩一句。先前他总天不亮就查窖温,夜里还对着账本盘算帮工的工钱,如今倒真成了“不操心”的人,只是吃饭时总盯着墙角那根竹探杆发愣。
没几日,王叔领着表伯们找上了门。都是沾亲带故的,谁家日子都紧巴,没了酒坊的活计,连买盐的钱都凑不齐,更别提拖欠的工钱了。“哥,咱偷偷开吧,就做街坊的生意,没人知道。”王叔搓着手说。父亲沉默半晌,终是叹了口气,重新掀开了酒缸上的棉布。
酒坊又热闹起来,蒸米的白汽、拌曲的声响、醇厚的酒香,悄悄漫回了巷子。父亲依旧把活计做得精细,只是收工后总会多张望几眼巷口。可安稳日子没撑过俩月,一个陌生男人推开了酒坊门,自称是税务员,说酒坊要交税,还要罚200元。
“200元?”父亲手里的竹探杆“当啷”掉在地上。那时全家一年到头忙活,收入也才20元。他连夜把酒缸、木甑低价卖给了邻村的杂货铺,又牵走了家里唯一的老黄牛,可凑来的钱连零头都不够。税务员走时撂下的话,像块石头压得他直不起腰。
那天晚上,父亲坐在空酒坊里,摸了摸冰冷的灶台,一夜没合眼。后来,巷口的木门再也没为酿酒开过,那些蒙着棉布的酒缸渐渐积满了灰,连空气里的酒糟香,都慢慢淡成了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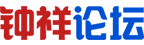

赞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