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夜的生死营救
暴雨夜的生死营救
四十多年了,那个暴雨倾盆的夏夜,至今想起来仍让我心有余悸。急促的敲门声像重锤般砸破寂静,门一开,浑身湿透的二柱跌撞着闯进来,声音嘶哑得几乎断裂:“田医生!快!俺娘快喘不上气了!再晚就来不及了!”
我抓起药箱就往门外冲,暴雨如注,雨点子像锋利的冰锥抽在脸上,泥泞的小路滑得如同抹了油,每走一步都要拼尽全力稳住身形。二柱背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狂奔,药箱在我怀里撞得生疼,里面的针头、纱布、几支急救针剂,是此刻能拉住老太太性命的唯一稻草。
赶到二柱家时,屋里挤满了焦急的乡亲,昏暗的油灯下,老太太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脸色紫得像熟透的茄子,嘴唇干裂泛白,胸口几乎不见起伏,只有喉咙里发出“赫赫”的喘鸣,像破旧的风箱在苟延残喘。她双手死死抓着床单,指甲泛白,眼神涣散,每一次呼吸都拼尽了全身力气,仿佛下一秒就要彻底断了气。“是急性哮喘大发作!”我心揪成一团,厉声让众人立刻散开,“都退后!别挡着空气!”
没有氧气瓶,我只能跪在床边,双手紧扣老太太的胸廓,一遍又一遍地做人工呼吸,每一次按压都用尽全身力气。紧接着,我颤抖着手抽出肾上腺素,消毒皮肤时指尖都在发抖,针头刺入的瞬间,我屏住了呼吸。做完这一切,我立刻拿出氨茶碱,小心翼翼地抽入针管,俯身在老太太耳边轻声安抚:“大娘,忍一忍,药推慢些,很快就不难受了。”药液缓缓推入静脉,我眼睛死死盯着老太太的脸,不敢有半分松懈。
汗水混着雨水顺着额头往下淌,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我却连眨眼都不敢。二柱在一旁哭得撕心裂肺,直跺脚,乡亲们大气不敢出,只有油灯的火苗在风中剧烈摇曳,映着满屋子惨白又焦灼的脸。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般漫长。突然,老太太剧烈地咳嗽了几声,接着缓缓睁开了眼睛,虽然依旧虚弱,却有了些许神采。屋里瞬间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欢呼声,有人甚至红了眼眶。
我瘫坐在地上,浑身的力气仿佛被抽干,这时才发现自己的赤脚早已被地上的碎柴禾划破,鲜血混着泥水渗出来,可我竟浑然不觉。二柱“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就要给我磕头,我赶紧拉住他,心里又酸又涩——那时的我们,凭着一双手、几样简单的器械,在生死边缘硬闯,靠的不仅是单薄的医术,更是乡亲们沉甸甸的信任。
后来每次想起那晚,我都记得油灯昏黄的光,记得老太太醒来时微弱却救命的呼吸,记得乡亲们眼里混杂着感激与后怕的泪水。那是赤脚医生最惊险的一夜,却也是最滚烫的记忆——我们踏着泥泞而来,背着药箱奔走,用最朴素的坚持,在生死线上抢回一条又一条鲜活的生命。
四十多年了,那个暴雨倾盆的夏夜,至今想起来仍让我心有余悸。急促的敲门声像重锤般砸破寂静,门一开,浑身湿透的二柱跌撞着闯进来,声音嘶哑得几乎断裂:“田医生!快!俺娘快喘不上气了!再晚就来不及了!”
我抓起药箱就往门外冲,暴雨如注,雨点子像锋利的冰锥抽在脸上,泥泞的小路滑得如同抹了油,每走一步都要拼尽全力稳住身形。二柱背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狂奔,药箱在我怀里撞得生疼,里面的针头、纱布、几支急救针剂,是此刻能拉住老太太性命的唯一稻草。
赶到二柱家时,屋里挤满了焦急的乡亲,昏暗的油灯下,老太太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脸色紫得像熟透的茄子,嘴唇干裂泛白,胸口几乎不见起伏,只有喉咙里发出“赫赫”的喘鸣,像破旧的风箱在苟延残喘。她双手死死抓着床单,指甲泛白,眼神涣散,每一次呼吸都拼尽了全身力气,仿佛下一秒就要彻底断了气。“是急性哮喘大发作!”我心揪成一团,厉声让众人立刻散开,“都退后!别挡着空气!”
没有氧气瓶,我只能跪在床边,双手紧扣老太太的胸廓,一遍又一遍地做人工呼吸,每一次按压都用尽全身力气。紧接着,我颤抖着手抽出肾上腺素,消毒皮肤时指尖都在发抖,针头刺入的瞬间,我屏住了呼吸。做完这一切,我立刻拿出氨茶碱,小心翼翼地抽入针管,俯身在老太太耳边轻声安抚:“大娘,忍一忍,药推慢些,很快就不难受了。”药液缓缓推入静脉,我眼睛死死盯着老太太的脸,不敢有半分松懈。
汗水混着雨水顺着额头往下淌,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我却连眨眼都不敢。二柱在一旁哭得撕心裂肺,直跺脚,乡亲们大气不敢出,只有油灯的火苗在风中剧烈摇曳,映着满屋子惨白又焦灼的脸。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般漫长。突然,老太太剧烈地咳嗽了几声,接着缓缓睁开了眼睛,虽然依旧虚弱,却有了些许神采。屋里瞬间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欢呼声,有人甚至红了眼眶。
我瘫坐在地上,浑身的力气仿佛被抽干,这时才发现自己的赤脚早已被地上的碎柴禾划破,鲜血混着泥水渗出来,可我竟浑然不觉。二柱“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就要给我磕头,我赶紧拉住他,心里又酸又涩——那时的我们,凭着一双手、几样简单的器械,在生死边缘硬闯,靠的不仅是单薄的医术,更是乡亲们沉甸甸的信任。
后来每次想起那晚,我都记得油灯昏黄的光,记得老太太醒来时微弱却救命的呼吸,记得乡亲们眼里混杂着感激与后怕的泪水。那是赤脚医生最惊险的一夜,却也是最滚烫的记忆——我们踏着泥泞而来,背着药箱奔走,用最朴素的坚持,在生死线上抢回一条又一条鲜活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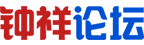

赞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