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气
小时候,常常为力气小而苦恼,因为力气比别人小,不管做什么事,不管怎么努力,其结果总是比人差一些,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其实,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只要你不怕辛苦,舍得下力,想搞外快并不难。那时候,供销合作社门市部门口常年都贴着各种农副产品以及药材和动物皮毛的品种和价格。每年冬至后,只要你吃得苦,晚上可以下夹子捕捉黄鼠狼,一张狼子皮可以卖四块多,也可以到河坡里去下炸弹,炸个狗獾狐狸啥的,其皮毛也不便宜,当年我们那河坡两岸灌木密布,是各种小型野生动物的家园,而炸弹火药及铁砂子供销社都可以买到。不过,这些都是大人们才敢做的事,小孩子们夜里是不敢到野外活动的,因为都怕鬼。
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也有赚外快的机会。不说每年春天抓蜈蚣的事,因为不仅仅是可以换钱,而且还是任务,而一旦上升到了任务,其积极性就没有那么高了,而为完成任务的心情常常会盖过卖钱的喜悦。因为你家伙不但长相恐怖狰狞,很多人都不敢抓,且若不慎被咬,那疼起来不是一般的难受。而除了这,我们来钱的途径还有两种,那就是挖药材和割药材。且这两种行当要简单的多,只要有力气就行。
那时候,我们那里荒山很多,山上都长有桔梗这种中药材。秋天的时候,有时星期天不上学时,我们就会扛着挖锄提着篮子上山去挖桔梗。挖桔梗虽然不需要太大力气,只要你能挥动挖锄就行,但却很考验人的腿脚功夫。为了能多挖点药材,要不停的在各个山头上转悠,一天下来,得走数十公里路,而一天下来也最多挖到半斤药材。那时候的桔梗手购价是四块多一斤,且还要把皮剥净,晒的干枯后才能去卖,所以,虽然一天辛苦后,看上去是挖了很多,而等晒干后,也不过几两而已,且卖的钱还不一定能进你的荷包。常常是大人们拿去卖了,钱就成了家里的了。
割窑柴就得到冬天茅草枯黄也后了。那时候,公社在我们东边的热包山下建有石灰窑厂,且常年收购窑柴。记得当时是一分到一分五一斤。星期天的时候,我们也会几个人一起结伴去割窑柴。那热包山非常陡峭,且满山都是裸露的石灰石,东一块西一块的,就像瘌痢头样,所以就叫它热包山。
别看它山这边陡峭且怪石嶙峋的,且山背后却很平坦,且都长满了茅草,到了冬天,却是一片金黄。割柴的时候却没啥,只是要将柴挑下山就不那么容易了。没办法,由于力气小,根本就不敢挑柴下山,就只好将柴捆好后滚下山来。这样不仅容易被挂掉一些柴火,有时还容易被滚散,且损失更大。所以在每次回家的路上盘点收人时,都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总是要比别人少些。记得从来没超过过一块,总是在八九毛角上徘徊。不过当时想,少就少点吧,也没啥不好意思的,这可都是能进自己荷包的。
十七岁那年的秋天,就得正式参加劳动了。当年由于个子不高,力气不济,着实吃了些苦头,受了些气。当年好羡慕那些大叔大哥们那挑草头的动作。打钎的时候,一插,一端,再一插,一端一甩就上了肩,走起路来,大步流星,肩上的草头的谷穗,也随着脚步的节奏一闪一闪的,非常潇洒。反观我们,打钎时得用胳臂将第一捆草头端起来时还得同时用脚把另一头踩在地上上肩后才能扎进另一捆将其挑起,非常笨拙。挑上肩后还的擎着,不敢那么大步流星,还得不停的换肩,若距离太远时,还得用双肩,像架飞机似的,别提多狼狈了。
好在18岁那年的秋天,我就离开的了家,也再也不用凭力气吃饭了。而经过两三年的休养生息,我人也长高了不少,力气也觉得大了不少。那时候,队里还有稻场,稻场里还有石磙。为了验证自己的力气,就只有到稻场里去竖石磙了。当时是竖了小头又竖大头,觉得不过瘾,竖了再推,推了在竖,还不时来个单手竖。那有力傍身的感觉,是真好。
25岁那年,我才正经使用了一回力气。那时,全省的棉花标准仿制工作在我们公司举行。时间是五月中旬至七月中旬,为期两个月。有我们下属的十二家公司和已经分离出去的荆门公司共十三家公司近两百人的规模。为此,国家给我们公司批了几千斤的粮食计划,而这些粮食计划到每年的五月底就要过期,必须得在五月三十一号前将粮食全部买回来。
记得那一年是一次性买了三千斤大米,共十五包。当时又没有小工,只能叫上我们两个年轻员工,开着生活用车到粮加里去提货。当时我还真有点发怵,两百斤一袋的大米包,还得扛上车,确实没什么把握。只是当真正扛起来时,却也没什么,感觉还挺好,觉得比刚回乡时交公粮的谷包要轻松多了,且一口气就扛了八包。
其后,有时候在做业务时也会和有些年轻的司机或搬运工们打赌扛棉夹。我们的棉花机夹非常紧实,每包在八十五公斤左右。不过一般只扛一件能证明有力就行了。
当跨过新世纪后,就再也没有抖过力了。
其实,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只要你不怕辛苦,舍得下力,想搞外快并不难。那时候,供销合作社门市部门口常年都贴着各种农副产品以及药材和动物皮毛的品种和价格。每年冬至后,只要你吃得苦,晚上可以下夹子捕捉黄鼠狼,一张狼子皮可以卖四块多,也可以到河坡里去下炸弹,炸个狗獾狐狸啥的,其皮毛也不便宜,当年我们那河坡两岸灌木密布,是各种小型野生动物的家园,而炸弹火药及铁砂子供销社都可以买到。不过,这些都是大人们才敢做的事,小孩子们夜里是不敢到野外活动的,因为都怕鬼。
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也有赚外快的机会。不说每年春天抓蜈蚣的事,因为不仅仅是可以换钱,而且还是任务,而一旦上升到了任务,其积极性就没有那么高了,而为完成任务的心情常常会盖过卖钱的喜悦。因为你家伙不但长相恐怖狰狞,很多人都不敢抓,且若不慎被咬,那疼起来不是一般的难受。而除了这,我们来钱的途径还有两种,那就是挖药材和割药材。且这两种行当要简单的多,只要有力气就行。
那时候,我们那里荒山很多,山上都长有桔梗这种中药材。秋天的时候,有时星期天不上学时,我们就会扛着挖锄提着篮子上山去挖桔梗。挖桔梗虽然不需要太大力气,只要你能挥动挖锄就行,但却很考验人的腿脚功夫。为了能多挖点药材,要不停的在各个山头上转悠,一天下来,得走数十公里路,而一天下来也最多挖到半斤药材。那时候的桔梗手购价是四块多一斤,且还要把皮剥净,晒的干枯后才能去卖,所以,虽然一天辛苦后,看上去是挖了很多,而等晒干后,也不过几两而已,且卖的钱还不一定能进你的荷包。常常是大人们拿去卖了,钱就成了家里的了。
割窑柴就得到冬天茅草枯黄也后了。那时候,公社在我们东边的热包山下建有石灰窑厂,且常年收购窑柴。记得当时是一分到一分五一斤。星期天的时候,我们也会几个人一起结伴去割窑柴。那热包山非常陡峭,且满山都是裸露的石灰石,东一块西一块的,就像瘌痢头样,所以就叫它热包山。
别看它山这边陡峭且怪石嶙峋的,且山背后却很平坦,且都长满了茅草,到了冬天,却是一片金黄。割柴的时候却没啥,只是要将柴挑下山就不那么容易了。没办法,由于力气小,根本就不敢挑柴下山,就只好将柴捆好后滚下山来。这样不仅容易被挂掉一些柴火,有时还容易被滚散,且损失更大。所以在每次回家的路上盘点收人时,都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总是要比别人少些。记得从来没超过过一块,总是在八九毛角上徘徊。不过当时想,少就少点吧,也没啥不好意思的,这可都是能进自己荷包的。
十七岁那年的秋天,就得正式参加劳动了。当年由于个子不高,力气不济,着实吃了些苦头,受了些气。当年好羡慕那些大叔大哥们那挑草头的动作。打钎的时候,一插,一端,再一插,一端一甩就上了肩,走起路来,大步流星,肩上的草头的谷穗,也随着脚步的节奏一闪一闪的,非常潇洒。反观我们,打钎时得用胳臂将第一捆草头端起来时还得同时用脚把另一头踩在地上上肩后才能扎进另一捆将其挑起,非常笨拙。挑上肩后还的擎着,不敢那么大步流星,还得不停的换肩,若距离太远时,还得用双肩,像架飞机似的,别提多狼狈了。
好在18岁那年的秋天,我就离开的了家,也再也不用凭力气吃饭了。而经过两三年的休养生息,我人也长高了不少,力气也觉得大了不少。那时候,队里还有稻场,稻场里还有石磙。为了验证自己的力气,就只有到稻场里去竖石磙了。当时是竖了小头又竖大头,觉得不过瘾,竖了再推,推了在竖,还不时来个单手竖。那有力傍身的感觉,是真好。
25岁那年,我才正经使用了一回力气。那时,全省的棉花标准仿制工作在我们公司举行。时间是五月中旬至七月中旬,为期两个月。有我们下属的十二家公司和已经分离出去的荆门公司共十三家公司近两百人的规模。为此,国家给我们公司批了几千斤的粮食计划,而这些粮食计划到每年的五月底就要过期,必须得在五月三十一号前将粮食全部买回来。
记得那一年是一次性买了三千斤大米,共十五包。当时又没有小工,只能叫上我们两个年轻员工,开着生活用车到粮加里去提货。当时我还真有点发怵,两百斤一袋的大米包,还得扛上车,确实没什么把握。只是当真正扛起来时,却也没什么,感觉还挺好,觉得比刚回乡时交公粮的谷包要轻松多了,且一口气就扛了八包。
其后,有时候在做业务时也会和有些年轻的司机或搬运工们打赌扛棉夹。我们的棉花机夹非常紧实,每包在八十五公斤左右。不过一般只扛一件能证明有力就行了。
当跨过新世纪后,就再也没有抖过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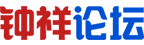

赞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