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儒、释、道三教并立,和尚与文士互不尊大,你说的话我不理解。”梅琦困惑地望着柯喜,不知他讲这个典故出于何意。
“种地和炊事工作本无尊卑,我舍此求彼其理一也。何为高?何为低?你完全没有必要抬高炊事工作而贬低种地的行业。”柯喜解释自己的意思。
“算了算了,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别人的意志是不能强加给他的。”梅琦说完向前走了两步,然后又停下转过身来,面对柯喜摇了摇头。
“听你的意思我还是很愚蠢了?”柯喜向前跟了两步,与转过身来的梅琦相向而立。
“叫我怎么说呢!从才思反应上说你很敏捷,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敏捷。这次你对待分配的态度我只能这么说了:智者千虑总有一失,愚者三思必有一得。不为浮云袭双眼,只要身真红心坚。你不为明摆着的这些利益所动,坚定的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生活,这是十分令人称道的。不过,只怕过后你会后悔。”
“后不后悔那是以后的事,起码眼下没让自己做不愿意做的事就不失为一个明智的决定。”柯喜笑了笑。
“你很倔犟。”梅琦说。那意味让人辨不清是戏谑还是在赞扬。
“还有呢?”柯喜感到梅琦的话语是那样的亲切,让他心情舒畅。
“好强词夺理。”梅琦又笑着说了一句。
“还有什么?”柯喜不依不饶。
“我也说不清。反正有一句话可以肯定:你是一个善于诡辩的人,一个诡辩的让人并不反感而且还受益匪浅的人。”梅琦说,心情很亢奋。
柯喜服从分配也罢,不服从分配好罢,考试招工是个全局性安排,领导对每个人的思想工作都是要做到家的。第二天上午,四十多岁的党委李委员在各部门有关领导的陪同下,再一次将几个参加分配的年轻人召集到一起,在说了几句必要的开场白后,就直接向几个参加分配的年轻人问道:“经过一夜的考虑,大家对昨天的分配没有什么意见吧?”
“没有。”除柯喜以外,几个参加分配的年轻人齐声回答,虽不响亮却很干脆。
“好,不仅要服从分配,而且还要干好,否则是要打板子的。”陪同的领导中有一人风趣地插了一句,给压抑的会场带来了几分轻松。
“你呢小柯?你考虑得怎么样?”李委员向低头坐在那里没有任何反应的柯喜问道。
“我不愿意。”柯喜抬头回答:“不合我性格的工作,我怕干不好有负领导对我的信任。”
“哎,你先干吧,以后再想办法调换工作。”参加这次分配的柯喜唯一的熟人曹秀梅急了。她虽然和柯喜是高中同学,但年龄却比柯喜足足大两岁。柯喜看起来还像个天真的少年,而她则是一个十分成熟的大姑娘了。
“我的事不用你管。”柯喜小声地回答,固执地摇了摇头。
“小柯,干什么工作都有个适应过程,你还年轻,相信你以后会明白的。”李委员语重心长,其意思是希望柯喜能够正确对待这次分配。
“我没想到考来考去最后是分配我去干炊事员,否则,我就不参加考试了。”柯喜的态度更加明朗。
“小柯,你可能不知道这次招工的炊事员是要送到外地进行专业培训,回来后就是外宾馆的掌勺大师傅。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而谋不到的肥差呀,你千万不要糊涂。”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干部就像大姐姐劝导不知事的小弟弟一样劝导着柯喜。
“谁想去就让谁去好了,反正我不去。”柯喜低着头,声音不大却很坚决地再一次明确了自己的态度。
“调换工作是不可能的,不干炊事员就意味着必须回去种地。”李委员态度和蔼,语气平平,但微笑的神情却让人明白他的话没有半点回旋余地。
“农村的孩子,权当是昙花一现,回去种地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我愿意回去种地。”柯喜不假思索,应声而答。
柯喜把话都说到了绝处,往下的工作当然也就不好做了。况且外宾馆的掌勺大师傅是个肥差,想干的人多的是,所以也没有必要再跟他多费口舌。年轻人心高气傲不了解生活的艰辛,不知道一口吃成个大胖子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他愿意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磨砺自己就让他去吧。也许多少年后他会反省今天的事情,会反省生活并不是想象的那样简单,会明白今天大家百般劝说他虽然是职责所在为了把工作搞好,同时也全是一片好意。但今天的柯喜思想是不会转弯了,起码他眼下就做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决定。
散会出来,时间已是十点半了。没有班车,更没有便车,柯喜甩开大步就向自己的村子走来。丘陵地带,层峦叠嶂,沟壑交融,蚓形山道蜿蜒在林中草丛。八月天气,稻谷含苞吐穗,花生饱粒进浆。争奇斗妍的山花已被春衔夏叼去,只有小小无名花姗姗来迟,默默绽放着深红色细碎之瓣,悄立在田间幽径,路旁水边,与荆棘为友,与小草做伴,无怨无悔,如火如炽。鸟儿没有争吵,秋蝉倒扯直嗓子喊了起来。柯喜无心观赏周围的景致,他低头盯着路面,迈着大步,转过几道弯,翻过几道梁,很快就钻到丘陵山水的怀抱里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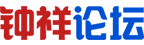

赞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