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哥家申
表哥家申
田埂上追逐的风声、树荫下嬉戏的笑语,是童年最鲜活的底色,而这底色里,始终映着表哥家申的身影。他属猴,我属鸡,大我一岁,是妈妈大舅的儿子。大舅曾是国民党部队的团长,起义后因思想问题入狱,家申家在夏营村,距我家龙虎庄仅两里路,地缘与血缘让我们从小便形影不离。
那时的“成份”像道无形的墙。表哥家虽有“伪人员”父亲,却划成了贫农;我家是地主成份,凡事都矮半截。上初中时,表哥学习稍逊于我,却顺利考入南阳十四中成为正式生,我只能去私立中学就读。后来考高中,表哥落榜待业,我借着父亲朋友的关系进入煤田地质学校,人生轨迹第一次出现清晰的分叉。
闹荒灾那年,河南青年纷纷外出谋生,表哥去了湖北洪湖的太同湖农场。那里每月能挣些钱,他写信催我过去,可我一心向学,终究没能赴约。表哥从小没下过地,农场的苦根本吃不住,几个月后便狼狈返乡。更沉重的是,大舅已病死在监狱,曾是军官太太的大舅妈另嫁他人,表哥和表妹不愿跟随,只能守着空荡荡的老屋,日子过得愈发清苦。
经小舅母介绍,表哥成了家。表嫂黑脸大眼,性子温顺得像春日的溪水,可表哥婚后总没好脸色,打骂是常事,表嫂却从不还口,默默扛起家务。表哥种地没兴致,转而种树,可树木遭虫害,果树不结果,他索性弃了果园,卖给了别人。
后来表哥做起花生买卖,收花生、跑运输,常常饥一顿饱一顿,几夜不合眼。起初赚了些钱,他倾尽所有加大本钱,渐渐攒下家底,盖起了楼房,日子总算有了起色。可安稳日子没过多久,表哥开始胃口变小、胃痛气闷,日渐消瘦得连站都站不稳。四处求医无果后,省医院的胃癌诊断像记重锤,短短半年,他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如今再想起表哥,童年的嬉闹、谋生的挣扎、日子好转又骤逝的遗憾,在记忆里交织成网。他的一生,像那个年代许多普通人一样,被成份、灾荒、生计裹挟着前行,拼尽全力抓住过希望,却终究没能握住晚年的安稳,只留下无尽的唏嘘,在田埂的风里轻轻回荡。
田埂上追逐的风声、树荫下嬉戏的笑语,是童年最鲜活的底色,而这底色里,始终映着表哥家申的身影。他属猴,我属鸡,大我一岁,是妈妈大舅的儿子。大舅曾是国民党部队的团长,起义后因思想问题入狱,家申家在夏营村,距我家龙虎庄仅两里路,地缘与血缘让我们从小便形影不离。
那时的“成份”像道无形的墙。表哥家虽有“伪人员”父亲,却划成了贫农;我家是地主成份,凡事都矮半截。上初中时,表哥学习稍逊于我,却顺利考入南阳十四中成为正式生,我只能去私立中学就读。后来考高中,表哥落榜待业,我借着父亲朋友的关系进入煤田地质学校,人生轨迹第一次出现清晰的分叉。
闹荒灾那年,河南青年纷纷外出谋生,表哥去了湖北洪湖的太同湖农场。那里每月能挣些钱,他写信催我过去,可我一心向学,终究没能赴约。表哥从小没下过地,农场的苦根本吃不住,几个月后便狼狈返乡。更沉重的是,大舅已病死在监狱,曾是军官太太的大舅妈另嫁他人,表哥和表妹不愿跟随,只能守着空荡荡的老屋,日子过得愈发清苦。
经小舅母介绍,表哥成了家。表嫂黑脸大眼,性子温顺得像春日的溪水,可表哥婚后总没好脸色,打骂是常事,表嫂却从不还口,默默扛起家务。表哥种地没兴致,转而种树,可树木遭虫害,果树不结果,他索性弃了果园,卖给了别人。
后来表哥做起花生买卖,收花生、跑运输,常常饥一顿饱一顿,几夜不合眼。起初赚了些钱,他倾尽所有加大本钱,渐渐攒下家底,盖起了楼房,日子总算有了起色。可安稳日子没过多久,表哥开始胃口变小、胃痛气闷,日渐消瘦得连站都站不稳。四处求医无果后,省医院的胃癌诊断像记重锤,短短半年,他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如今再想起表哥,童年的嬉闹、谋生的挣扎、日子好转又骤逝的遗憾,在记忆里交织成网。他的一生,像那个年代许多普通人一样,被成份、灾荒、生计裹挟着前行,拼尽全力抓住过希望,却终究没能握住晚年的安稳,只留下无尽的唏嘘,在田埂的风里轻轻回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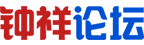

赞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