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灯下的生命守望
昏黄的油灯在土坯墙上摇摇晃晃,把白河水的影子拉得很长。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这位村里唯一的男赤脚医生,总背着磨得发亮的药箱,穿梭在泥泞的田埂间。当村里最后一个接生婆远嫁河东,产妇们的生死便沉甸甸地压在了他的肩头。
他忘不了那两个喝农药的妯娌。抢救时插导尿管的瞬间,重度会阴撕裂的伤痕刺得人眼疼——那是旧时接生陋习留下的烙印,让女人们一辈子被尿漏缠身。油灯下,白河水攥紧了拳头,灯光在他眼底跳动:“得用新法接生,不能再让姐妹们遭这份罪。”
七组杨小姑家的二媳妇临盆那晚,产妇撕心裂肺的痛呼像针一样扎进耳朵。床沿边的杨小姑急得直搓手,眼看着胎头已露,却因会阴太紧卡得死死的。白河水蹲下身,指尖抚过紧绷的产道,突然拿出手术刀。“咔”的一声轻响,划开皮肉的声音很轻,却像劈开了生与死的界限。他双手稳稳护住会阴,直到第一声婴儿啼哭炸响,一屋人憋了半天的气终于化作欢腾——那个在油灯下诞生的小生命,仿佛给昏暗的土房镀上了层金光,白河水抹了把满脸的汗,心里热得发烫。
大雪封门的那个冬夜,四组的产妇疼得在土炕上打滚。白河水摸黑赶来,一查是胎位不正。公社医院远在十里外,积雪没到膝盖,根本走不了。产妇颤抖的呻吟像冰锥扎心,他俯下身,指尖在方寸之间游走、调整,每一次触碰都精准如钟表齿轮。从深夜两点到次日午后,当婴儿的啼哭终于撞碎风雪,产妇家属递来的粗瓷碗里,鸡蛋还温着。
最险的是徐家产妇的双胞胎。白河水守了一天加半夜,油灯芯结了好几次灯花。第一个胎儿的脐带绕颈三圈,他屏住呼吸,指尖像解绳结般慢慢褪,一圈、两圈、三圈……直到那小小的脖颈终于舒展。晨光涌进窗棂时,第二个婴儿的啼哭混着鸡叫一起响起,他才发现白大褂早已被汗水浸透,腰像断了似的疼,却奇怪地不觉得累。徐家为了留记念白河水接出的一双胎儿,把这一对双儿名改为徐大双和徐小双。
村里人总说,那天听见婴儿哭的时候,好像看见死神悄悄退到了门外。而白河水只是揉了揉发酸的腰,对着递来鸡蛋的家属,露出个疲惫却踏实的笑。油灯的光落在他沾着血污的白大褂上,映出满室的温暖——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总有人捧着一颗心,在昏黄的灯光下,与死神掰着手腕,守望着一个又一个新生。
他忘不了那两个喝农药的妯娌。抢救时插导尿管的瞬间,重度会阴撕裂的伤痕刺得人眼疼——那是旧时接生陋习留下的烙印,让女人们一辈子被尿漏缠身。油灯下,白河水攥紧了拳头,灯光在他眼底跳动:“得用新法接生,不能再让姐妹们遭这份罪。”
七组杨小姑家的二媳妇临盆那晚,产妇撕心裂肺的痛呼像针一样扎进耳朵。床沿边的杨小姑急得直搓手,眼看着胎头已露,却因会阴太紧卡得死死的。白河水蹲下身,指尖抚过紧绷的产道,突然拿出手术刀。“咔”的一声轻响,划开皮肉的声音很轻,却像劈开了生与死的界限。他双手稳稳护住会阴,直到第一声婴儿啼哭炸响,一屋人憋了半天的气终于化作欢腾——那个在油灯下诞生的小生命,仿佛给昏暗的土房镀上了层金光,白河水抹了把满脸的汗,心里热得发烫。
大雪封门的那个冬夜,四组的产妇疼得在土炕上打滚。白河水摸黑赶来,一查是胎位不正。公社医院远在十里外,积雪没到膝盖,根本走不了。产妇颤抖的呻吟像冰锥扎心,他俯下身,指尖在方寸之间游走、调整,每一次触碰都精准如钟表齿轮。从深夜两点到次日午后,当婴儿的啼哭终于撞碎风雪,产妇家属递来的粗瓷碗里,鸡蛋还温着。
最险的是徐家产妇的双胞胎。白河水守了一天加半夜,油灯芯结了好几次灯花。第一个胎儿的脐带绕颈三圈,他屏住呼吸,指尖像解绳结般慢慢褪,一圈、两圈、三圈……直到那小小的脖颈终于舒展。晨光涌进窗棂时,第二个婴儿的啼哭混着鸡叫一起响起,他才发现白大褂早已被汗水浸透,腰像断了似的疼,却奇怪地不觉得累。徐家为了留记念白河水接出的一双胎儿,把这一对双儿名改为徐大双和徐小双。
村里人总说,那天听见婴儿哭的时候,好像看见死神悄悄退到了门外。而白河水只是揉了揉发酸的腰,对着递来鸡蛋的家属,露出个疲惫却踏实的笑。油灯的光落在他沾着血污的白大褂上,映出满室的温暖——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总有人捧着一颗心,在昏黄的灯光下,与死神掰着手腕,守望着一个又一个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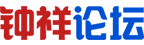

赞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