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月光
椅
如水月光笼罩着村子的大树,房舍,猪崽,羊圈,鸡舍,和这块残碑。残碑来自清嘉庆年间,族人集资修缮祠堂所立的。手轻轻一碰,族人先辈的光影似乎鲜活起来,瞬时又离开。只是知道,族人先辈是从东边而来,可能是兵燹,可能是逃荒和其他原因。先辈只给我们留下了这款残缺的碑文,在嘈杂的世俗中还述说着当年的清空注视着如今的风月。偶尔,我们只是觉得内疚,摇摇晃晃的岁月中我们不小心把祖宗弄丢了。我想会不会可能是这样的。
那一年秋天。
家族的老少通过围猎,采摘,获得了很多食物。鉴于功劳和才能,先辈们一直推介了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做家族长老,目的为了获得更多食物。长老犹豫之间,族人的木匠,发挥自己的特长做了一把檀木椅将长老按在了椅子上。
星起暮归,晴耕雨做。
家族在长老的带领下,很快兴盛起来,人口也多了起来,随之面临的问题也多了起来,长老命令木匠族人带领至分支去别的地方打猎,这一去就是好多年。木匠回来时候,带回来很多食物,可是为食物的派发操起了干戈,纷争中,木匠一把凿子把长老打死了。追随长老的那只家族人在郁郁中西迁,带走的只是家族的家谱。
木匠坐上了那把他自己手工做的椅子。
木匠很快老了,可是为了继承他位置的人族人却着急起来。有的说木匠的大儿子顺子可代替,有的说木匠的二儿子狗子可以接替,也有的说村里放羊的傻子也可以候选的。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傻子消失在族人眼帘中的,没有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只是知道他离开前带走了族的一个家谱,带着他的妻儿老小往村里大槐树的南方跑了。
木匠的大儿子和二儿子,看着他们父亲冰冷的尸体和那把檀木椅子对峙起来。檀木椅子是父亲唯一留给他们唯一的遗产。
顺子拿起一把斧头,狗子顺手垫起来一把弯月刀。
狗子走了,据说去了某个岛。狗子他不后悔在湾月刀落下的一瞬他犹豫停顿了会,而这一瞬时却换来他狗腿重重的斧头一击。
顺子坐上了檀木椅。
顺子的檀木椅在星光中摇曳起来,很多人说顺子的檀木椅子好看,吸引了好多的观者,也带来了外族的一个人的窥探。
星河万年,斗转一瞬。
顺子在外族的火药中到下了。族人在兵燹中纷纷夺命,族人的二大爷纷难中抢回了几张燃着的家谱,看着那张历经沧桑的檀木椅子,二大爷咬咬牙,抬了起来,放上了牛车,加入到了西奔逃难的队伍。
二大爷死了,是饿死的,据说他是为了省口粮食给拉车的牛吃。
二大爷的尸体刚冷,檀木椅光鲜地在异地温暖地放了下来。随之,祠堂,家谱,还有碑文。
那个冬天,一把大火燃了起来,檀木椅子,家谱,宗祠还有祖宗长老的排位,在泪眼中化为黑灰蝴蝶,远远地,远远地飞走了,据说远在岛上的狗子的后代小狗子似乎还看见了黑灰蝴蝶的飞扬。
DNA,大数据,头,视屏等科技含量高的名词一夜之间涌起了春潮,潮水也漫过了乡村先辈的那块残碑。可怕的是有的科技意义上的头集聚为圈,制做了些悖伦理的事情。更多民众遵循着,我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信仰什么。 面对现状我们也不知道望哪里去,犹豫中也曾思考,若当年先辈们若有这些技术和科技狠活该多好,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有一条脉络清晰的线路,乃至视屏,记录着先辈们的人事变更,岁月长河的变迁再变迁,该有多好。变了的是空间,不变的是流淌在先辈灵魂深处的血脉,仰望星空,秦汉的月,唐明的境,民国的风似乎还在的。
狗
家里来了只狗。
娘盛了碗饭。
狗不吃。
娘又夹了块骨头。
饭剩。
娘摆摆头,现在狗子大米饭都不吃了,原来的狗子人类大便都吃的。
狗和我们还是友好地处了下来。
狗莫名地在稻谷场或稻田里狂吠,有时候是对峙而吠,寻声而去,一切安然,什么也不见。狗咬空,狗已疯,老话说的。有人说我们的狗疯了。狗任然太阳升起的时候跑出去,星空燃起的时候归来。终于,有天狗叼回来只死去的小鸡,仪式感慢慢丢在我的面前,似乎还在示意我吃那只蛆芽满满地小鸡。看着我愕然的样子,狗又叼起死去的小鸡充我走进两步。我几乎是火冒三丈操起一根棒子,狗跑,鸡落。想着,狗子也是番好心,不了了之。后来狗子又在家里捉了几只老鼠,和老鼠崽。然后大嚼,只落下鼠尾巴。
狗和小鸡崽能安然地相处的。家里几只小鸡,它们和狗能供处一碗吃食物的,有时候狗还绅士般让小鸡先吃食物,小鸡礼让着狗,几番推让后,小鸡似乎还领狗子的情,犹豫片刻就大吃食物,能把最好的骨头留给狗子。
家里的伙食,随着炊烟的变化而变化,简朴的犹如碗清水。不是每顿饭都有肉吃的,有时候是素菜。
娘仍然盛碗带白菜汤的大米饭给狗吃。
狗不吃。
娘任然坚持几乎每天重复。
狗子不吃素食饭菜的大米饭,你还给它干什么?
娘说,给,是我的责任,吃,是狗子的选择。
终于,有天狗子吃起了钟祥的米茶。
都是饿的,饱的,才让它们变了。
我想起了儿时家里曾养过的几只猫,饿了土豆,酸菜,大米饭都吃的,据说现在有的猫粮的口感都不适合猫变化的胃口了。我在村里发现了只小猫,流浪猫,是饿死的,我几乎自责地夹起猫的尸体将它扔进了垃圾堆。
麻将
乡村的文化是惨白乏味的,通常从麻将开始,到斗地主结束,只是中途多了几杯茶。
摇摇晃晃的茶汤中,乏着骨牌和纸牌的影子。起初的安静终被赢和输的氛围捣乱,在吵杂声中终止了一天的精神寄托,赢家忙着数着赌筹,输家几乎掀起了桌子,并试着发誓,再也不赌了,再赌就把手剁掉。通常一顿饭的功夫就忘记了自己的诺言,人,又坐上了麻将桌子。小孩子在吵杂的麻将声中,忙着更换做作业的桌子位置。
通常这都是以各自家为载体进行的。
后来村有了文化室。村里共建的。有书籍,有棋牌,有电视。
更妙的是每家还多了个小喇叭,手把长长的绳索开关一拉,声音就弥漫了房内。难忘的是早六点半,伴随着歌唱祖国音乐的声起,那是熟悉的节目,通常为那个时候守候,听着遥远的声音,才知道世界离我们好近又好远。人们也乐于评价着风靡一时的电视剧或新闻,或试着探讨水稻小麦的技术。
一夜之间,喇叭坏了,布满灰尘的喇叭,终丢在了风里,文化室也在风雨中坍塌了。
人们又捡起了麻将。
办厂的刘大叔一个麻将的杠上开花,赢了一块钱。他得意地大笑起来,声音越来越大,终叹下一口气,沉沉地倒在麻将桌上。大叔走了,永远地走了。那一块钱留给了谁,不知,只知道大叔带着永久地笑意走的。
做豆腐的李婶,输了10块钱,脸象三冬的茄子,推到麻将牌的她慌忙着找灶台,却发现一锅豆腐错过了点浆的最佳时机,早已熬成了一锅浆糊。
五岁的小王,已经能准确识别并喊出红中的麻将牌。
70岁的老关为一张牌出错懊悔,说可以更好的。虽然赢了。旁边的乡亲数落着他,怎么打的牌。
年轻的文山以此为契机,以自家的空房子开启了麻将馆,还管茶水和中午一顿饭。听说,收入,还能养家糊口。似乎是一阵风的时间,常来打牌的人不来了,有的跑到了镇上打牌,有的躲在了自己的家里,更多地聚在了网上。文山的茶馆落寂了。文山似乎听见近的远的麻将声,望着自己闲置的几台自动麻将机桌子,他摇摇头,我哪里做错了?
守村人
一个傻笑,又迎来了一个太阳,新的一天开始了。
二傻子慌乱而无序地穿着衣服,带他穿好后发现裤子却穿反了。无奈,只好脱下重新来过。二傻子,有个官方的名字叫守村人。这一名字是似乎统一的,适合每个乡村。
吃完早饭,喂好鹅,鸡,猫,二傻子牵着羊和狗要出门了。他知道村子哪里的草最嫩,水最清。偶尔还能遇见村里的朝哥在哪里放羊,朝哥比他大半个世纪,按辈分二傻子仍然能含含糊糊叫他朝哥。稻谷起来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几乎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基本是二傻子和朝哥这样的老弱病残的人。
“二,山上有狼,多机灵点啊。”朝哥远远地招呼着二傻子。
“嗯啦,嗯啦”二傻子欢快地笑着,狗也欢快地撒着欢。
是一个下午,二傻子在狗的带路下发现朝哥跌入到半悬崖的,下面还有只羊羔。
二傻子飞快跑回村,支支吾吾地说着,打麻将的几个老头终明白,拿着绳索和棍子找到朝哥,绳子提起他的一瞬,朝哥缓缓说了句,二呀,是人。头一歪,就走了。
唢呐声响起来,朝哥在固定的风俗程序中走着终成一个盒子。人们低沉着脸。朝哥刚从广东打工回来的两个儿子似乎看不出悲伤,只有二傻子哭的像个泪人。
晚上,二傻子睡不着觉。不是第一天这样了。他看着窗户外面的月光,寻思着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山的那边,还是山?羊的那边,还是羊?没有了朝哥的作伴,羊,怎么办?焦虑中的二傻子,拿起一张纸,歪歪扭扭画上一只羊,两只羊,顺手叠起了一架纸飞机,轻轻地一划,空气中似乎弥漫起羊的味道,纸飞机轻盈地从窗户飞到外面去了。
二傻子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的,听说手里还握着架纸飞机。
我轻轻地合上手中的电脑,无奈而又无助地发呆。乡村,承载了日月星辰的乡村,在一暮暮潮起潮落的光影中坠落或升起,面对现状困惑我们能做什么?乡村的血脉在现代风潮中徘徊踯躅。致敬那些消失的光影和存在的光影,你们让我们知道活着的乡村,是有希望的。
天正蓝,草正青。
如水月光笼罩着村子的大树,房舍,猪崽,羊圈,鸡舍,和这块残碑。残碑来自清嘉庆年间,族人集资修缮祠堂所立的。手轻轻一碰,族人先辈的光影似乎鲜活起来,瞬时又离开。只是知道,族人先辈是从东边而来,可能是兵燹,可能是逃荒和其他原因。先辈只给我们留下了这款残缺的碑文,在嘈杂的世俗中还述说着当年的清空注视着如今的风月。偶尔,我们只是觉得内疚,摇摇晃晃的岁月中我们不小心把祖宗弄丢了。我想会不会可能是这样的。
那一年秋天。
家族的老少通过围猎,采摘,获得了很多食物。鉴于功劳和才能,先辈们一直推介了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做家族长老,目的为了获得更多食物。长老犹豫之间,族人的木匠,发挥自己的特长做了一把檀木椅将长老按在了椅子上。
星起暮归,晴耕雨做。
家族在长老的带领下,很快兴盛起来,人口也多了起来,随之面临的问题也多了起来,长老命令木匠族人带领至分支去别的地方打猎,这一去就是好多年。木匠回来时候,带回来很多食物,可是为食物的派发操起了干戈,纷争中,木匠一把凿子把长老打死了。追随长老的那只家族人在郁郁中西迁,带走的只是家族的家谱。
木匠坐上了那把他自己手工做的椅子。
木匠很快老了,可是为了继承他位置的人族人却着急起来。有的说木匠的大儿子顺子可代替,有的说木匠的二儿子狗子可以接替,也有的说村里放羊的傻子也可以候选的。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傻子消失在族人眼帘中的,没有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只是知道他离开前带走了族的一个家谱,带着他的妻儿老小往村里大槐树的南方跑了。
木匠的大儿子和二儿子,看着他们父亲冰冷的尸体和那把檀木椅子对峙起来。檀木椅子是父亲唯一留给他们唯一的遗产。
顺子拿起一把斧头,狗子顺手垫起来一把弯月刀。
狗子走了,据说去了某个岛。狗子他不后悔在湾月刀落下的一瞬他犹豫停顿了会,而这一瞬时却换来他狗腿重重的斧头一击。
顺子坐上了檀木椅。
顺子的檀木椅在星光中摇曳起来,很多人说顺子的檀木椅子好看,吸引了好多的观者,也带来了外族的一个人的窥探。
星河万年,斗转一瞬。
顺子在外族的火药中到下了。族人在兵燹中纷纷夺命,族人的二大爷纷难中抢回了几张燃着的家谱,看着那张历经沧桑的檀木椅子,二大爷咬咬牙,抬了起来,放上了牛车,加入到了西奔逃难的队伍。
二大爷死了,是饿死的,据说他是为了省口粮食给拉车的牛吃。
二大爷的尸体刚冷,檀木椅光鲜地在异地温暖地放了下来。随之,祠堂,家谱,还有碑文。
那个冬天,一把大火燃了起来,檀木椅子,家谱,宗祠还有祖宗长老的排位,在泪眼中化为黑灰蝴蝶,远远地,远远地飞走了,据说远在岛上的狗子的后代小狗子似乎还看见了黑灰蝴蝶的飞扬。
DNA,大数据,头,视屏等科技含量高的名词一夜之间涌起了春潮,潮水也漫过了乡村先辈的那块残碑。可怕的是有的科技意义上的头集聚为圈,制做了些悖伦理的事情。更多民众遵循着,我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信仰什么。 面对现状我们也不知道望哪里去,犹豫中也曾思考,若当年先辈们若有这些技术和科技狠活该多好,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有一条脉络清晰的线路,乃至视屏,记录着先辈们的人事变更,岁月长河的变迁再变迁,该有多好。变了的是空间,不变的是流淌在先辈灵魂深处的血脉,仰望星空,秦汉的月,唐明的境,民国的风似乎还在的。
狗
家里来了只狗。
娘盛了碗饭。
狗不吃。
娘又夹了块骨头。
饭剩。
娘摆摆头,现在狗子大米饭都不吃了,原来的狗子人类大便都吃的。
狗和我们还是友好地处了下来。
狗莫名地在稻谷场或稻田里狂吠,有时候是对峙而吠,寻声而去,一切安然,什么也不见。狗咬空,狗已疯,老话说的。有人说我们的狗疯了。狗任然太阳升起的时候跑出去,星空燃起的时候归来。终于,有天狗叼回来只死去的小鸡,仪式感慢慢丢在我的面前,似乎还在示意我吃那只蛆芽满满地小鸡。看着我愕然的样子,狗又叼起死去的小鸡充我走进两步。我几乎是火冒三丈操起一根棒子,狗跑,鸡落。想着,狗子也是番好心,不了了之。后来狗子又在家里捉了几只老鼠,和老鼠崽。然后大嚼,只落下鼠尾巴。
狗和小鸡崽能安然地相处的。家里几只小鸡,它们和狗能供处一碗吃食物的,有时候狗还绅士般让小鸡先吃食物,小鸡礼让着狗,几番推让后,小鸡似乎还领狗子的情,犹豫片刻就大吃食物,能把最好的骨头留给狗子。
家里的伙食,随着炊烟的变化而变化,简朴的犹如碗清水。不是每顿饭都有肉吃的,有时候是素菜。
娘仍然盛碗带白菜汤的大米饭给狗吃。
狗不吃。
娘任然坚持几乎每天重复。
狗子不吃素食饭菜的大米饭,你还给它干什么?
娘说,给,是我的责任,吃,是狗子的选择。
终于,有天狗子吃起了钟祥的米茶。
都是饿的,饱的,才让它们变了。
我想起了儿时家里曾养过的几只猫,饿了土豆,酸菜,大米饭都吃的,据说现在有的猫粮的口感都不适合猫变化的胃口了。我在村里发现了只小猫,流浪猫,是饿死的,我几乎自责地夹起猫的尸体将它扔进了垃圾堆。
麻将
乡村的文化是惨白乏味的,通常从麻将开始,到斗地主结束,只是中途多了几杯茶。
摇摇晃晃的茶汤中,乏着骨牌和纸牌的影子。起初的安静终被赢和输的氛围捣乱,在吵杂声中终止了一天的精神寄托,赢家忙着数着赌筹,输家几乎掀起了桌子,并试着发誓,再也不赌了,再赌就把手剁掉。通常一顿饭的功夫就忘记了自己的诺言,人,又坐上了麻将桌子。小孩子在吵杂的麻将声中,忙着更换做作业的桌子位置。
通常这都是以各自家为载体进行的。
后来村有了文化室。村里共建的。有书籍,有棋牌,有电视。
更妙的是每家还多了个小喇叭,手把长长的绳索开关一拉,声音就弥漫了房内。难忘的是早六点半,伴随着歌唱祖国音乐的声起,那是熟悉的节目,通常为那个时候守候,听着遥远的声音,才知道世界离我们好近又好远。人们也乐于评价着风靡一时的电视剧或新闻,或试着探讨水稻小麦的技术。
一夜之间,喇叭坏了,布满灰尘的喇叭,终丢在了风里,文化室也在风雨中坍塌了。
人们又捡起了麻将。
办厂的刘大叔一个麻将的杠上开花,赢了一块钱。他得意地大笑起来,声音越来越大,终叹下一口气,沉沉地倒在麻将桌上。大叔走了,永远地走了。那一块钱留给了谁,不知,只知道大叔带着永久地笑意走的。
做豆腐的李婶,输了10块钱,脸象三冬的茄子,推到麻将牌的她慌忙着找灶台,却发现一锅豆腐错过了点浆的最佳时机,早已熬成了一锅浆糊。
五岁的小王,已经能准确识别并喊出红中的麻将牌。
70岁的老关为一张牌出错懊悔,说可以更好的。虽然赢了。旁边的乡亲数落着他,怎么打的牌。
年轻的文山以此为契机,以自家的空房子开启了麻将馆,还管茶水和中午一顿饭。听说,收入,还能养家糊口。似乎是一阵风的时间,常来打牌的人不来了,有的跑到了镇上打牌,有的躲在了自己的家里,更多地聚在了网上。文山的茶馆落寂了。文山似乎听见近的远的麻将声,望着自己闲置的几台自动麻将机桌子,他摇摇头,我哪里做错了?
守村人
一个傻笑,又迎来了一个太阳,新的一天开始了。
二傻子慌乱而无序地穿着衣服,带他穿好后发现裤子却穿反了。无奈,只好脱下重新来过。二傻子,有个官方的名字叫守村人。这一名字是似乎统一的,适合每个乡村。
吃完早饭,喂好鹅,鸡,猫,二傻子牵着羊和狗要出门了。他知道村子哪里的草最嫩,水最清。偶尔还能遇见村里的朝哥在哪里放羊,朝哥比他大半个世纪,按辈分二傻子仍然能含含糊糊叫他朝哥。稻谷起来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几乎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基本是二傻子和朝哥这样的老弱病残的人。
“二,山上有狼,多机灵点啊。”朝哥远远地招呼着二傻子。
“嗯啦,嗯啦”二傻子欢快地笑着,狗也欢快地撒着欢。
是一个下午,二傻子在狗的带路下发现朝哥跌入到半悬崖的,下面还有只羊羔。
二傻子飞快跑回村,支支吾吾地说着,打麻将的几个老头终明白,拿着绳索和棍子找到朝哥,绳子提起他的一瞬,朝哥缓缓说了句,二呀,是人。头一歪,就走了。
唢呐声响起来,朝哥在固定的风俗程序中走着终成一个盒子。人们低沉着脸。朝哥刚从广东打工回来的两个儿子似乎看不出悲伤,只有二傻子哭的像个泪人。
晚上,二傻子睡不着觉。不是第一天这样了。他看着窗户外面的月光,寻思着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山的那边,还是山?羊的那边,还是羊?没有了朝哥的作伴,羊,怎么办?焦虑中的二傻子,拿起一张纸,歪歪扭扭画上一只羊,两只羊,顺手叠起了一架纸飞机,轻轻地一划,空气中似乎弥漫起羊的味道,纸飞机轻盈地从窗户飞到外面去了。
二傻子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的,听说手里还握着架纸飞机。
我轻轻地合上手中的电脑,无奈而又无助地发呆。乡村,承载了日月星辰的乡村,在一暮暮潮起潮落的光影中坠落或升起,面对现状困惑我们能做什么?乡村的血脉在现代风潮中徘徊踯躅。致敬那些消失的光影和存在的光影,你们让我们知道活着的乡村,是有希望的。
天正蓝,草正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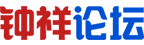

赞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