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寨那个台子

曹寨那个台子
2024年1月14日,侄儿子三周年后急急忙忙回钟祥,经过这个地方。这是个稍近路。大哥和他的女儿觉着我走路不方便坚持要送我,他有一辆电瓶四轮车。我告诉他们,不需要,我虽然走路艰难,但是必须走。有一段时间脚底下好像垫了厚厚的棉花,走不成路。到中医院看医生,就是五楼那位负责体检的医生,问我要检查什么,我一走让他看。他呵呵一笑,脑梗。说是搞个CT,我说干脆核磁共振。他好了好脉搏,就组方剂。逐渐可以歪歪扭扭了。孩子们觉得大医院来得快,先是协和后是同济。协和服三个月药,说是一吃完就好了,可是觉得没用,有严重的趋势。同济比较客观,大体是不必管它,开的是三七之类的药,说是用一个月。后来看来不管是不行的,就继续请中医院医生治疗。用了三个月药,情况就向好的方向转化。快过年了,干脆中断一段时间不用药,争取坚持到开春。如有不妥,赶紧找他不就是了嘛。到1月14日,已经停药22天。大哥不放心情理之中。他们以为我走正常的路,可是我走的是捷径。他们到了红英路口,没见我,觉得我不会那么快,就电话我。我告诉他们走的是捷径。就拍了这张照片发给他们。他们就赶过来依然要送我。我当然坚持走,他们跟着我,看着我走。一起说着闲话。到路边等车,让他们回去,可以放心了吧,可是大哥说,我看着你上车。
经过曹寨这个台子的时候,台子的南边是个大坑,望着坑南的那排房屋,有种想去看看的心情。那是舅家。舅舅舅母早不在了,几个舅老表依次摆开。不是因为要接孙子,是不会这么匆匆忙忙的。下次吧。
有一年回河南到了淅川县,淅川没有忘记因为丹江大坝把我们洒落在湖北大柴湖的这些朋友,他们建了移民纪念馆。曹寨当时似乎还没有完工,有一张照片记忆着他们的规划。
2024年1月14日,侄儿子三周年后急急忙忙回钟祥,经过这个地方。这是个稍近路。大哥和他的女儿觉着我走路不方便坚持要送我,他有一辆电瓶四轮车。我告诉他们,不需要,我虽然走路艰难,但是必须走。有一段时间脚底下好像垫了厚厚的棉花,走不成路。到中医院看医生,就是五楼那位负责体检的医生,问我要检查什么,我一走让他看。他呵呵一笑,脑梗。说是搞个CT,我说干脆核磁共振。他好了好脉搏,就组方剂。逐渐可以歪歪扭扭了。孩子们觉得大医院来得快,先是协和后是同济。协和服三个月药,说是一吃完就好了,可是觉得没用,有严重的趋势。同济比较客观,大体是不必管它,开的是三七之类的药,说是用一个月。后来看来不管是不行的,就继续请中医院医生治疗。用了三个月药,情况就向好的方向转化。快过年了,干脆中断一段时间不用药,争取坚持到开春。如有不妥,赶紧找他不就是了嘛。到1月14日,已经停药22天。大哥不放心情理之中。他们以为我走正常的路,可是我走的是捷径。他们到了红英路口,没见我,觉得我不会那么快,就电话我。我告诉他们走的是捷径。就拍了这张照片发给他们。他们就赶过来依然要送我。我当然坚持走,他们跟着我,看着我走。一起说着闲话。到路边等车,让他们回去,可以放心了吧,可是大哥说,我看着你上车。
经过曹寨这个台子的时候,台子的南边是个大坑,望着坑南的那排房屋,有种想去看看的心情。那是舅家。舅舅舅母早不在了,几个舅老表依次摆开。不是因为要接孙子,是不会这么匆匆忙忙的。下次吧。
有一年回河南到了淅川县,淅川没有忘记因为丹江大坝把我们洒落在湖北大柴湖的这些朋友,他们建了移民纪念馆。曹寨当时似乎还没有完工,有一张照片记忆着他们的规划。

残存的记忆--在东坪(做客1)
总是要过年的。我对于年的最早的记忆是到我的舅家做客。下面说的究竟是不是一定在过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我也不敢确认,不过,我是觉得和年有关的。
我的舅家住在东坪的西北边,他们是曹寨大队的一个叫下头的地方。我从我的那个盐行向北走大概一里左右就到了我的那个老东头。紧靠老东头的西边是条南北向流淌的大河,据说是叫石岩河。那河没有桥,我过河的方法也没有了记忆。只知道在过河的位置向东看我的老东头,有个很高的斜面,河里有船,是那种一叶扁舟类型的。我见到过一叶扁舟的船头屹立着几只鱼鹰,艄公用长长的竹竿插入水里,那腰一弯,那船就向前驶去很远。那艄公用竹竿拍打着水面,溅起些水花,那鱼鹰就飞起来,很快地一头扎入水中。不一会儿,那鱼鹰嘴里夹着鱼----不大,头尾扑闪着,跳到船头,站在那里。那艄公抱起鱼鹰,一只手拿住鱼鹰的脖颈,一只手就拿下了那鱼。然后就放了鱼鹰,那鱼鹰仍然飞向空中,盘旋着,又一头扎入水中。
过了河,地势比较平坦。据说那个地方叫东洼。有一条向西北走的路,经过一个山坡,不知道走了多远,从直向西的地方穿过去,是个油坊。我的舅舅就在这里做工。打油的。舅舅怎么接待我的,我完全没有了记忆,总之,我在油坊里玩,那油坊有个大蒸笼,有若干蒸格,摞得高高的,冒着白烟。人们把格子抱下来,倒出格子里的东西,用白布包裹起来,包的圆圆的样子,放入木制的器具中。那木制的器具方方正正的,很大,有不少的格子,格子放满了,舅舅和他的同事,拿起厚厚的大大的木楔,使劲的往格子的两头楔入。楔入了个头,稳定了,就抡起大锤,使劲的砸那木楔,一直到把那木楔砸进格子里。
应该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了吧。那餐吃的是面条。舅舅给我盛了一大碗,端到那格子的下面,他拿了一个葫芦瓢,放到格子的下面,然后拿了一个木楔,插入格子的一头,砸下去,顺着格子的一头,就是放着葫芦瓢的位置,芝麻油就流淌了出来。舅舅接了满满的一瓢油,乐呵呵的往我的碗里倒。我的碗里的面条被那油浸得油渍渍的。在家的时候,母亲给我碗里放油,都是几滴,那香就够令我满意的。到了油坊,这么多的油倒到我的碗里,呵呵!
我高兴坏了,端起碗,夹起面条就往嘴里送进去。可是,不香!可不是嘛,油多了,就是不香,不过,这个经验这个时候没有。我连连说不香,舅舅和他的同事们哈哈大笑起来。
楼主| 发表于 2010-2-21 15:38:58
残存的记忆---在东坪(做客2)
我家是四条汉子,舅家也有四条汉子,不过,舅母比我的母亲多了个小闺女。我在我家属老三,舅家的老三比我小一岁。在舅家做客,是我做客次数最多的地方。后来,我参加工作了,到了城里,老婆没跟来,我也大多到我的大老表家里做客。大表嫂说“外甥子是舅家的狗”,大概说得是实情。这个时候在舅家做客,我对大老表没有印象,二老表大我一些,看看我和三老表下棋,嘻嘻哈哈而已。
我们下的是军棋,开始是明棋,就是把棋子扣在格子上,先手翻开一个棋子,这个棋子就是人家了。所以,一般翻第一个棋子,总是在没有“军营”的地方翻。我和三老表的精神都是高度的紧张,二老表总是为我出出主意,又为三老表出出主意。当然,我比三老表大一点,我就赢的盘数多一些。明棋来烦了,就来暗棋。就是把各自的棋子摆在自己的一方,要考虑到进攻或防守时不吃亏,前沿阵地对阵的五颗字总是想了又想。军棋总是放在各自的左右角,总是有地雷在拱卫着。
舅家住在半坡上。玩烦了,就往下走,没几步路,就是个小弯子,似乎很有几户人家。那里有个稻场,稻场的边缘照例有麦秸跺,石磙子之类的东西。大舅家就住在这里。大舅家是几个女孩,都是白白净净的。圆圆的脸蛋,粉红粉红的。穿得也很惹眼,也比我讲卫生得多。总之是我的盐行的家乡,除了那个改娃(WER,二声)可以媲美之外,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
做客的记忆是十分美好的。
楼主| 发表于 2010-2-25 09:28:16
残存的记忆---在东坪(做客3)
舅家的人都是诚实真诚的人,没有任何弯弯绕。大人们有时候拉着我的双手唱儿歌,说是“筛萝萝,扬场场,舅舅来了吃啥饭,打鸡蛋,烙油鲜(馍),不吃不吃两大碗。
”,母亲听到这话总是分辩说,你舅舅可不是这样的人,倔得很,说走就走,拉也拉不住,很难留他吃饭。舅舅个子不大,精瘦得紧,总是乐呵呵的,1990年的78月间,我在客店搞社教,舅舅离开了我们,母亲没告诉我,我总是觉得遗憾。
舅母也很好,小时候大概对于脸色很关注。我能够经常到舅家,乐此不彼,大概就是没有见过舅母给我过脸色。很普通的家庭妇女,总是笑嘻嘻的。现在的聪明人一说起那个时候生活那么紧张,我就诧异。果如是,舅母家哪有余粮供我经常光顾啊。
最有意思的就是三老表了。我们下棋是自不必说的。在舅家玩了几天。就想回家了,我就要三老表送我回家。这一送就送到我的那个盐行,然后我再送他回家。一送就送到他的那个下头。以至于大人们抗议了,说是你们送来送去,送到什么时候啊。这件事被大人们说了许多年,也笑了许多年。
三老表送我回家,没有走老东头那条路。他是从舅家的半坡下来,经过大舅家,继续向南走。不知道走了多远,有一个很大很宽的深沟,沟底有细细的水流。我们下沟速度很快,上沟就很吃力。不知道谁说过过沟遇到鬼让背过河的故事,我对于这道沟的记忆如此清新。过了这条沟,我怎么回到我的家,我就说不上来了。我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这算是从曹寨自房营回到东坪的一条路。后来,我的梦中经常出现走到一个山坡,不知道如何走的情况,我就疑心是这条我记得这条沟的路的一个景色。
看来,走路,记路,也是很重要的。
总是要过年的。我对于年的最早的记忆是到我的舅家做客。下面说的究竟是不是一定在过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我也不敢确认,不过,我是觉得和年有关的。
我的舅家住在东坪的西北边,他们是曹寨大队的一个叫下头的地方。我从我的那个盐行向北走大概一里左右就到了我的那个老东头。紧靠老东头的西边是条南北向流淌的大河,据说是叫石岩河。那河没有桥,我过河的方法也没有了记忆。只知道在过河的位置向东看我的老东头,有个很高的斜面,河里有船,是那种一叶扁舟类型的。我见到过一叶扁舟的船头屹立着几只鱼鹰,艄公用长长的竹竿插入水里,那腰一弯,那船就向前驶去很远。那艄公用竹竿拍打着水面,溅起些水花,那鱼鹰就飞起来,很快地一头扎入水中。不一会儿,那鱼鹰嘴里夹着鱼----不大,头尾扑闪着,跳到船头,站在那里。那艄公抱起鱼鹰,一只手拿住鱼鹰的脖颈,一只手就拿下了那鱼。然后就放了鱼鹰,那鱼鹰仍然飞向空中,盘旋着,又一头扎入水中。
过了河,地势比较平坦。据说那个地方叫东洼。有一条向西北走的路,经过一个山坡,不知道走了多远,从直向西的地方穿过去,是个油坊。我的舅舅就在这里做工。打油的。舅舅怎么接待我的,我完全没有了记忆,总之,我在油坊里玩,那油坊有个大蒸笼,有若干蒸格,摞得高高的,冒着白烟。人们把格子抱下来,倒出格子里的东西,用白布包裹起来,包的圆圆的样子,放入木制的器具中。那木制的器具方方正正的,很大,有不少的格子,格子放满了,舅舅和他的同事,拿起厚厚的大大的木楔,使劲的往格子的两头楔入。楔入了个头,稳定了,就抡起大锤,使劲的砸那木楔,一直到把那木楔砸进格子里。
应该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了吧。那餐吃的是面条。舅舅给我盛了一大碗,端到那格子的下面,他拿了一个葫芦瓢,放到格子的下面,然后拿了一个木楔,插入格子的一头,砸下去,顺着格子的一头,就是放着葫芦瓢的位置,芝麻油就流淌了出来。舅舅接了满满的一瓢油,乐呵呵的往我的碗里倒。我的碗里的面条被那油浸得油渍渍的。在家的时候,母亲给我碗里放油,都是几滴,那香就够令我满意的。到了油坊,这么多的油倒到我的碗里,呵呵!
我高兴坏了,端起碗,夹起面条就往嘴里送进去。可是,不香!可不是嘛,油多了,就是不香,不过,这个经验这个时候没有。我连连说不香,舅舅和他的同事们哈哈大笑起来。
楼主| 发表于 2010-2-21 15:38:58
残存的记忆---在东坪(做客2)
我家是四条汉子,舅家也有四条汉子,不过,舅母比我的母亲多了个小闺女。我在我家属老三,舅家的老三比我小一岁。在舅家做客,是我做客次数最多的地方。后来,我参加工作了,到了城里,老婆没跟来,我也大多到我的大老表家里做客。大表嫂说“外甥子是舅家的狗”,大概说得是实情。这个时候在舅家做客,我对大老表没有印象,二老表大我一些,看看我和三老表下棋,嘻嘻哈哈而已。
我们下的是军棋,开始是明棋,就是把棋子扣在格子上,先手翻开一个棋子,这个棋子就是人家了。所以,一般翻第一个棋子,总是在没有“军营”的地方翻。我和三老表的精神都是高度的紧张,二老表总是为我出出主意,又为三老表出出主意。当然,我比三老表大一点,我就赢的盘数多一些。明棋来烦了,就来暗棋。就是把各自的棋子摆在自己的一方,要考虑到进攻或防守时不吃亏,前沿阵地对阵的五颗字总是想了又想。军棋总是放在各自的左右角,总是有地雷在拱卫着。
舅家住在半坡上。玩烦了,就往下走,没几步路,就是个小弯子,似乎很有几户人家。那里有个稻场,稻场的边缘照例有麦秸跺,石磙子之类的东西。大舅家就住在这里。大舅家是几个女孩,都是白白净净的。圆圆的脸蛋,粉红粉红的。穿得也很惹眼,也比我讲卫生得多。总之是我的盐行的家乡,除了那个改娃(WER,二声)可以媲美之外,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
做客的记忆是十分美好的。
楼主| 发表于 2010-2-25 09:28:16
残存的记忆---在东坪(做客3)
舅家的人都是诚实真诚的人,没有任何弯弯绕。大人们有时候拉着我的双手唱儿歌,说是“筛萝萝,扬场场,舅舅来了吃啥饭,打鸡蛋,烙油鲜(馍),不吃不吃两大碗。
”,母亲听到这话总是分辩说,你舅舅可不是这样的人,倔得很,说走就走,拉也拉不住,很难留他吃饭。舅舅个子不大,精瘦得紧,总是乐呵呵的,1990年的78月间,我在客店搞社教,舅舅离开了我们,母亲没告诉我,我总是觉得遗憾。
舅母也很好,小时候大概对于脸色很关注。我能够经常到舅家,乐此不彼,大概就是没有见过舅母给我过脸色。很普通的家庭妇女,总是笑嘻嘻的。现在的聪明人一说起那个时候生活那么紧张,我就诧异。果如是,舅母家哪有余粮供我经常光顾啊。
最有意思的就是三老表了。我们下棋是自不必说的。在舅家玩了几天。就想回家了,我就要三老表送我回家。这一送就送到我的那个盐行,然后我再送他回家。一送就送到他的那个下头。以至于大人们抗议了,说是你们送来送去,送到什么时候啊。这件事被大人们说了许多年,也笑了许多年。
三老表送我回家,没有走老东头那条路。他是从舅家的半坡下来,经过大舅家,继续向南走。不知道走了多远,有一个很大很宽的深沟,沟底有细细的水流。我们下沟速度很快,上沟就很吃力。不知道谁说过过沟遇到鬼让背过河的故事,我对于这道沟的记忆如此清新。过了这条沟,我怎么回到我的家,我就说不上来了。我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这算是从曹寨自房营回到东坪的一条路。后来,我的梦中经常出现走到一个山坡,不知道如何走的情况,我就疑心是这条我记得这条沟的路的一个景色。
看来,走路,记路,也是很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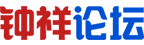

赞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