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百科,对虫的定义严格限制在无脊椎的范畴里。因此,我们家将蛇识为一条加长版的虫,显然有点欠思量。
不过,名哉,称呼也。
在那个没有筛选能力,连老师授课都操持着浓厚乡音的环境里,过分的苛刻于学名与昵称的是与非,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了。
我与蛇接触不多,这并不是我俩的缘分不深。
在它面前,我就好比赵忠祥动物世界里的一只小山羊:“某日,不期而遇,明知今生已休矣,既不跑亦不躲。
不跑不躲,不能理解为我这人临危不惧。
而是在和秃头上那双勾魂的眼、对视的瞬间、浑身都麻酥酥的,两条腿根本不听使唤。”
这种猫鼠情结的养成,主要得宜于我妈的学龄前教育。
现在的小孩超幸福,娱乐活动多:“好动的,去动植物园逛逛;习静者,宅在家里还能看看动画片。”
以前,我们几乎没什么选项。因此男孩子都被养得猴哩狠:“下水摸鱼、上树掏蛋,个个都是一把好手。”
不过,我,是一个例外。
村里识字的人不多,男耕女织的生活模式经久没变过。
即是农闲,没有不良嗜好的男哩,每天就在农田里反复的捣腾;女哩则‘猫’在家里摸哈针线活。
我的父母生活格调比他们高。常常忙里偷闲,蹲在门口的石墩上,捧着一本不是缺页少字,就是被撕掉了书皮儿的线装书,津津有味的啃个不停。
成长在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家庭,自然对农村的这些雕虫小技不屑一顾。
父母一有空就跟佛祖念金箍咒似的,弄一些似是而非的故事来约束我们的言行举止:“某某,下河捞鱼,跳下去后再也没有爬上岸了;某某,爬树滕钻屋檐掏鸟蛋,蛋没掏到,一条蛇赤溜一声钻进了他的嘴里了。”
说得有鼻子有眼,不由我不信。
问题是,摸鱼掏蛋这是一个基本功,很多娱乐活动都和它息息相关。不练就这项最基础的功能,很多有意义的情趣也都会与之擦肩而过。
以至于成年后,很多同龄人跟猴子似的,仅用两手就能“嗖嗖嗖”的泅到树梢;而我即是把手抠进了树干里,两三米高的树冠,对我来说仍是可望而不及的。
无法确定蛇对我持何态度,我严格的将我俩囚定在黑白二界。
我这人行事风格相对含蓄,但在对蛇问题上却从未含糊过。这种决绝的理念,主要基于“叶公好龙”的教训,我不想让叶公的事儿,在我这儿重演。
‘怵’,一方面源于父母的上述耳濡目染;二一个,课文<<农夫与蛇>>这则经典的寓言故事,对我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故事曰:“农夫寒夜晚归,偶遇冻僵的蛇。心生怜悯,捧起,放怀里暖之。蛇醒,咬农夫一口,夫亡。
原文已模糊。
但是,自从接触了这篇脍炙人口的寓言,蛇的猥亵得一塌糊涂的形象就从来没有改变过。这种经久不弃的态度,如果当初教我这篇寓言的老师知道了,应该感到很欣慰才是。
不过,这则原篇寓言,跟现在网络上诸多副本比,它的不完整性也不容忽视。
比如:原版只告诉了我们夫亡,没有交待蛇的去向;而副本除了明确“蛇死、夫亡外”,还着重的强调了,他们离开后,农夫的灵魂升上了天堂,毒蛇则下到了地狱里。
其二,副本在保证“绝不能怜悯像蛇一样的恶人”三观不变的情况下,还告诉了我们:“蛇这家伙虽然名声臭,但是除了它的食材,只有在自己可能受到威胁时,才会进行先发制人的主动攻击的这个基本常识。”
这处说词很重要。
如果属实,那么蛇蝎虽毒,在它获救后的攻击本意是值得商榷的。
这方面人就比它强多了。
有的,即使把龌龊事做尽。任何时候,在个人华丽的形象这门功课上是慎之又慎的。
其次,在对忘恩负义这组词意的栓释上,我认为跟<<东郭先生和狼>>中的主角比,后者更有张力。
因为狼在得救后,不仅全无感恩之心,还厚颜无耻的要借用先生的肉体“充饥”。这股肆无忌惮的贪婪,将狼身上的那股赤裸裸的流氓像昭然诺揭。
当然,我在这儿,只是试图对几个不同观念做些糅合,没想过要给谁谁谁鸣不平。
何况,帮蛇翻案我即没有情感这个基础,亦没有翻案所必须的理论和实践能力。
因为,当初老师的敦敦教导,就象烧红的烙铁,深深的镌刻在了心灵的深处,让我打心眼里排斥和厌恶这个不识好歹的东西。
而与排斥和厌恶同列的则是忌讳。
忌讳,是一种保全面子的临时性措施,换算成通俗的语言就是一个“怕”字。
如果此前经历仅是闻其声,冇谋其面的话。
那么另一次偶遇,却在我稚嫩的心上,留存了一堵无法抹去的阴影。
七八岁左右,我储存的并记忆不多。
一件是某日在空阔的稻场上玩嗨了,在有了回家的意识时,已不能自抑。跟个醉汉似的,边走边困。一不留神足下踩空,咕隆隆滚到了旁边的池塘里,把混浊的水美美的饱饮了一顿。
忆不起是谁把我捞起来的。
一觉醒来,赤条条的龟缩在一个硕大的簸箕里,浑身没有片叶遮挡,这种尴尬和形秽,被周围的一帮穿针引线的娘娘们一览无疑。
所以,再大点,心底就跟堵了一块‘物什’似的,耿耿于怀。
我觉得农村出来的娃们都很造孽!在华丽的衣裳内,仅剩一付皮囊而已。
因为男人们最精华的部分,全被这些提前“懂事”的二货们,投射过来的的余光给吸跑了。
另一件事儿,算得上是一件刻骨铭心的历史事件。
连续几天阴雨。
大清早,外面一阵的嘈杂声:“决堤了……,涨水了……!”
矫激奇诡,我破门而出。
果然,房前屋后,白茫茫的一片。
水,经过之处,浅处也足足淹没了人的膝盖。
我们家距大江大河远。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即是水龙王开恩,在雨水季节丢下几滴猫泪,也会瞬间被饥渴的大地吸收了。而农田的灌溉,则需要黄河定时定量的调度。由此可见涝是无法想象的。
然而,一切都在卜算之外!
所以,人们乐啊!尤其是我们这群还光着腚到处乱窜的人儿。
虾兵蟹将太多了,一群群一队队,跟阅兵似的。
之前这些还渴望而不可及的小东西,此刻竟毫不顾忌的,在我们的脚踝处蹭来蹭去。
人也多。
每个人手里,还多了一件趁手的家什:捞鱼的网兜、盛菜的篮子、淘米的筛子、晒粮食的簸箕……。
我,是一个豁了嘴的、用木瓜制成的“瓢”。
这瓢,薄而轻,但结实得狠。不过它盛水还行,如果作为一个捕鱼的工具,脑袋就有些智障了。
因为别人手里的器具:在水里一舀,端起,水便会在这起落间漏掉。
而我这个瓢。下水前轻飘飘的,使很大的劲往下戳,才能到达一个理想的深度;而出水时,又总是盛上来满满的一瓢水。先小心翼翼的倒掉混浊的水,才能看清瓢底的东西。
当然,这些也只是现在有了一定的逻辑能力后,通过比较才换算出二者的之,当时任何行为都只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一跳入水里,仿佛嗅到了这些红尾巴的鲤鱼、扁平的串条子在油锅里翻腾时散发出的肉香味。
因此,,望着一拨拨的鱼群,呆立了很长时间,才想起手中的家什。
于是,攥紧瓢把,追着鱼群将去的方向抄起一瓢。
真的捞起了一条哩!只不过这是个软不溜秋的家伙!
它,不知道是兴奋还是恐慌,操持着柔软的身材,不停的在瓢底疯狂的舞着。
“虫?……长虫!”
大唬。
腿跟灌了铅似的,即不敢向前,亦不能后退。站在原址,扯开嗓子就嚎起来。
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在这一次亲密交往中,我的形象被它糟蹋得一塌糊涂。
此后还有过多次邂逅相遇。
比如,某日正行进中,忽然公路的中央,横亘一具被碾得稀烂的遗骸。
这样的偶遇,较好处置。先让同伴用柴棍将其挑离,我再“从容”而过,基本上能保证风度不失。
另一种遭遇,却非常的尴尬和棘手。
这小东西虽然“舍哩狠”,但有吉祥的时候。
据说,如果某夜,它突然光临寒舍。那么就预示着,不久的将来不是有艳遇,就是要大发了。
人就是这么虚伪。虽然我对它常忧心惸惸,但有时另一股念想也常在胆田下翻腾。
果然,某日正酣,这小东西不期而至。
只不过,讨嫌哩狠,没一点素质。一会儿脖子、一会儿裤腿到处乱窜。
慌乱中,拚命地用脚压住被角,它又转至“被”沿处。
情势之下,伸出双手、揪着尾巴、使劲的将它从睡袍中拽出,象掷铅球似的扔出窗外。
然,另一条又趁虚而入。
折腾了半夜,搞哩人大汗淋淋、精疲力竭。
唬起。
梦,戛然而止。
呆立床边,提着被角抖抖,方再入眠!
跌覆的心,经多时调节,复归静怡。
然,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清早,饰粉电曰:“三更半夜,不好好休息到处乱窜。”
“啥意思,你在说我吗?”我问。
“不说你,说老球!”
“咋了,冇干坏事啵!”我问。
“冇,看见你跟一只老虎玩得嗨哩狠。”
“**,会不会做梦!”
“查遍咱们几千年的中国史。跟老虎玩,没吃过亏的也就武松一人。
深更半夜,你把我和虎爷弄到一块儿,这小命还会在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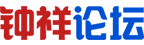

赞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