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城 佳 人 莫 愁 女
石 城 佳 人 莫 愁 女
莫愁女,战国末期楚国郊郢石城(今钟祥市郢中镇)人,是著名的歌舞艺术家,对楚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有过重大影响。但由于年代久远,地域变迁,加之当时的文献资料难于寻觅,尤其是后世的一些文人墨客随意附会,竟使得一个本来不应该混淆的历史人物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以致除了钟祥之外,南京和洛阳也似乎当真都有过莫愁。近年来,还有人不尊重史实,不仅否认莫愁女出生于楚国古城,而且杜撰出了梁武帝萧衍追求莫愁女为妃的所谓“纯情纪实”长篇小说,真是令人匪夷所思。那么,莫愁女究竟何许人也?本文力求正本清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样做,不仅后人将纠正谬误,而且也希望真正的莫愁女不再继续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可魂兮归来兮。
一
古都云开白雪楼,汉水还绕石城流。
何人知道寥天月,曾向朱门送莫愁。
(唐?胡曾《石城怀古》)
古代的钟祥称石城。《地理通释》中有明确的记载:“郢州子城三面墉基皆天造,正西绝壁,下临汉江,石城之名本此。”《狱地纪胜》中也说:“莫愁村,在汉江之西,地多桃花,春末花落,流水皆香。”《钟祥县志》其《古迹》篇记得更确切:“莫愁村,在汉西二里,古汉水经城址,其西为村,为莫愁所居地,城北有湖,与村毗邻,称莫愁湖。”
其实,莫愁女所居住的村庄,因为年年桃花盛开,红如簇云,人们称之为桃花村。莫愁湖原本称沧浪湖。桃花村与石城西门外的渡口绝壁上的白雪楼和楼东不远的阳春台隔江相望。莫愁女的父亲卢公,在汉江上摆渡,母亲在家中植桑种桃。莫愁女大约出生于楚顷襄王初年(公元前298年)左右。据说,她出生时天降暴雨,风大浪急,卢公收了船在家中照顾妻女,见女儿总是哭啼,便抱着她,一边用一个小小雀玉饰品轻轻搔她的脑袋,一边哼歌哄她:“莫哭啊,莫哭;莫悲啊,莫悲;莫愁啊,莫愁……”,没想到当她听到“莫愁”二字时,竟一下子停止了哭声,卢公就把她叫做“莫愁”。也正因如此,前人才有诗云:“金雀玉搔头,生来唤莫愁。”(明?张宁)
莫愁女天生一副金嗓子,卢公也一反前人的传统和卢家合族人的劝告,没让她学习种植和女工,而是从小就把她送进阳春台去习舞唱歌,当她长到十五六岁时,不仅出脱得象一株亭亭玉立的出水芙蓉,而且在歌舞上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金嗓一歌声嗽玉,霓裳一舞袖吐虹”就是对她生动的写照。特别是她在文艺巨匠屈原和宋玉的指导和帮助下,翻古传高曲,融楚辞乐声,历经波折,终于继大琴师刘涓子之后,完成了寡和之曲《阳春白雪》的合乐入歌传唱,使得本来绚丽多姿的楚文化又锦上添花,流出下了一首千古名曲。
莫愁女的歌舞声誉传遍了石城,自然也传进了楚王的宫苑。楚顷襄王把她征进设在兰台的王宫中作了歌舞姬,还把她的恋人王襄哥流放到了几千里外的扬州。“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这篇《莫愁女》生动记述了莫愁女泪别王襄哥的情景。滚滚南流的汉江水,洗不尽莫愁女思恋情人的哀愁,她对于在宫苑里唱歌跳舞供达官贵人们消遣娱乐的生活很快厌倦,在无可奈何时,她含愤从白雪楼上纵身跳入了汉江。
出人意外的是,莫愁女并没有被淹死,而是落水之后被在下游不远处打鱼的渔夫救起来了。她曾到扬州寻找过王襄哥,可惜心爱的人因思念她被折磨而死。他又不能回故乡,只好流落民间,为黎民百姓唱歌。莫愁女的歌深受人们的喜爱,“家家迎莫愁,人人说莫愁。莫愁歌一字,恰恰印心头。”(明?王世贞)正因为莫愁女的歌声唱进了人们的心里,所以人们在听了她的歌以后会情不自禁的倾其所有赠给她,没想到越是这样,莫愁女越发不安,“十万作缠头,莫愁不肯留。银钱黯欲尽,翻为莫愁愁。”(明?王世贞)她只得足无定踪,漂泊四方。直到晚年,她才悄悄回到故乡。当她得知父母由于思念和劳累早已去世,几间老屋因年久失修也已倒塌时,强撑了多年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在忧郁和贫病中,莫愁女静静地离开了人世,被乡邻们草草掩埋在莫愁湖边。
人们感念莫愁女的为人和品德,便把桃花村改名为莫愁村,把沧浪湖改名为莫愁湖,还把她时常行走的一条小路命名为莫愁路
二
罗绮晴骄绿水洲,芙蓉花外夕阳楼。
楼中日日歌声好,不及卢家有莫愁。
(明?李维祯《莫愁村》)
莫愁女虽然离去了,但她留下的歌却被人们世代传唱,直到终于被写进了正史。据南朝《宋书》记载:义帝刘义隆元嘉年间,臧质任竟陵郡内史(职同太守)治石城时,“余尝登石城,见群少年歌莫愁谣,因作《石城乐》、《莫愁乐》,咏莫愁故事。”而《唐书?杂志》则说:“石城乐,宋臧质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质尝为竟陵郡守,于城上眺瞩,见群少年歌谣通畅,因作此曲……《莫愁乐》,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石城乐?和》中复有‘莫愁’声,故歌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双桨,催送莫愁来……”梁武帝萧衍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年)冬,将石城的《莫愁乐》带到了南京,经过改造后,又搬进了皇宫。梁武帝时任乐官的陈智匠在《古今乐录》中说:“《莫愁乐》亦云《蛮乐》旧舞十六人,梁八人。”唐代时,经过乐官的严格审定,《莫愁乐》、《石城乐》、《阳春白雪》都进入了宫廷乐坊司。“百尺兰台气象雄,批襟况有大王风;诗人亦自分余劲,白雪歌声遍国中。”(清?毛会建)正因如此,自唐以来,万代诗人吟咏不绝。
“石城昔为莫愁乡,莫愁魂散石城荒。帆去帆来风浩渺,花开花谢春悲凉。”
(唐?郑谷)“石城湖上美人居,花乐笙歌春恨余。独自楼台对公子,晚风秋水落芙蕖。”(唐?元稹)“清江一曲抱村流,南国佳人字莫愁。此地从来可乘兴,酒杯无日不淹流。”(明?李维祯)“石城西畔莫愁湖,谁道当年女姓卢?遣愁愁向莫愁湖,愁向莫愁愁更愁”(清?刘泽宏)
如果说这些绝句已经很酣畅地表达了人们对莫愁女的怀念和惋惜之情的话,那么宋朝著名文学家王安石在其《登郢州白雪楼》一诗中,则更清晰地展现了当年的情景:“朱楼碧瓦何年有,榱桷连空欲惊矫。郢人烂漫醉浮云,郢女参差蹑飞鸟。”而宋朝末年的周密在《莫愁》词中,表现得更加细腻:“瑞云盘,翠侵妆额;眉柳嫩,不禁愁积;返魂谁染东风笔,写出郢中春色。人去后,垂扬自碧;歌舞梦,欲寻无迹;愁随两桨江南北,日暮石城风急。”
莫愁女的歌谣被传唱了千百年,莫愁女的故事更是在她的家乡广为流传,因而使得后人感慨万千。明代嘉靖初年的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袁宗皋,曾担任过兴王府右长史,在石城生活过多年,写下了许多吟颂郢中石城风物古迹的诗篇,他的《莫愁古渡》颇有深意:“如何一歌女,名远数千秋。多少英雄士,冥冥一土丘。”诗文共传誉,人地两留芳。墨愁女与她的家乡一起,千载弛誉,万世名扬。宋人洪迈在他的《容斋随笔》中写道:“莫愁者,郢州石城人,尽郢有莫愁村,画工传其貌,好事者多写寄四远。”
这些点缀于浩瀚典籍之中的“珍珠”,不仅十分清楚地记载了莫愁女的身世和影响,而且为后人研究莫愁女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三
沧浪渡口莫愁乡,万顷寒烟水落霜。
珍重使君留客意,一樽荒酒醉斜阳。
(宋?王之望《郢州怀古》)
按说,莫愁女的生平与家乡,在各种典籍中记载得非常明白,又有那么多的诗词歌赋在吟咏。为什么还会出现关于她的“南京”、“洛阳”等说法呢?追根求源,问题还是出在萧衍和周邦彦两大名人身上。
梁武帝萧衍,不仅是梁朝创立者,而且在位长达47年之久。他长于文学,又精通乐律,还擅长书法,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他在金陵建邺称帝后,曾写下过许多诗赋,尽管那些作品大都失传了,但仍有一些被流传下来,其中就有那首著名的《河中之水歌》。此“歌”开头两句就是:“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梁武帝将莫愁女“钦定”成了“洛阳的女儿到了金陵”。所以1500年来,人们以为他唱的当真是金陵故事,就把莫愁女当成了洛阳人,只是后来到了南京,而他真正的家乡却反倒被遗忘了。也正因如此,才会有萧衍追求莫愁女为妃之类的“纪实文学”作品公然出台(详见《中国故事》1989年第1期《拆不散的情侣》一文),可见其谬误影响何其深远。
其实,萧衍唱的既不是金陵故事,更不是他自身的所谓爱情故事。他之所以要这么唱,是与他的身世遇际分不开的。关于他的生平,《梁书》、《南史》、《资治通鉴》等史著均有明确的记载。如《南史?梁本纪上第六》:“梁高祖武皇帝讳衍……永元三年二月,南康王为相国,以帝为征东将军。戊申,帝发襄阳……留弟伟守襄阳城……移檄建邺,阐扬武威。及至竟陵,进屯九里……(九里即今钟祥市郢中镇东九华里处的九里回族自治乡政府所在地,作者注)”梁武帝萧衍之父萧顺之与齐高皇帝萧道成为好友,他们是同宗同族的弟兄,他们的发迹地就在石城周围。萧衍少时追随竟陵王萧子良,在石城一带生活过很长时间,自然早已熟悉了莫愁女的故事,他进金陵后,偶然感怀,写下了那首歌,不料被人们一直奉为真谛,从未有人对此提 过正面质疑,连《辞海》都只是模棱两可地同意了各种说法。
被后代词人奉为宗师的南宋大家周邦彦,字美成,其名篇《西河?金陵》曰:“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墙遥度无限。断压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沉半垒。夜深月过女墙来,伤心东望汉水。酒旗戏鼓甚处市?详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处;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
周邦彦不仅把战国时的楚国莫愁说成了南北时期的金陵莫愁,而且还将郢中的石城当成了南京金陵的石头城。这就给人以错觉:莫愁女既然在南京系过艇子,那她当然就是南京的人了。
其实,对于他们的疏忽,前人早就指出来了。知识渊博且熟悉历代掌故的南宋文学家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莫愁者,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近世周美成《西河》一阕专咏金陵,所云‘莫愁艇子曾系’之语 ,岂非误指石头城为石城乎?曾留下《儒林外史》的清代著名小说家吴敬梓也说:“出三山门外半里许,有莫愁湖,相传妓名莫愁者居此,因以为名。然梁真武帝诗云:洛阳女儿莫愁,则不应在此。其所以传闻者,以石城二字。按楚有石城,莫愁居之,亦非此石城。”尽管有许多谬误,但莫愁女的家乡是怎么也不会改变的。“沧浪渡口莫愁村,莫愁村中连莫愁湖,莫愁湖边芦花卢家台。”(明?钟惺)这既是一首诗,也是一幅简明的地图。莫愁村自明代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汉江改道后被摆到了汉水东岸,卢家台一直留存到期1935年,后遭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冲毁,但直到今天,居住在卢家台附近的人还能清楚地说出其遗址的具体位置。
“远度碧桃花,倚鞭白骏马。客程无暇问,先访莫愁家。”(明?王世贞)系缆石城下,孤吟怀暂来。江入桡艇子,将谓莫愁来。”(唐?蒋吉)这就是人们追念莫愁女的真实写照。
当然,《莫愁乐》是中化民族的乐舞,莫愁女是炎黄子孙的莫愁。南京和洛阳之所以要争莫愁女这个名人,除了希望提高当地的知名度外,更主要的还是说明了今天的人们对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崇尚。这一点,可能也是莫愁女这位石城绝代佳人所梦寐以求的夙愿吧。
/救命/无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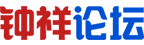

赞过的人